中国文学里,有类似于俄罗斯【圣愚】和日本【物哀】这样的概括性的趋同性审美概念吗?其他国家有类似的吗?
尽管悲喜不相通,但人类的境遇和反应常相似得出奇。物哀的主体是有意识地从日常营苟中退身并在各种风物里体味情绪涟漪的歇心人,圣愚是被神棍强行扣了个高帽的尚未被老天爷饿死的瞎家雀儿。当一个人利用物象对应并放大了自身的悲苦,那他就成了用血手帕掩着嘴去看梅花的肺结核,当一个人被别有用心的阴谋机构或草台班子托胳肢窝赶鸭上架,那他就成了背贞洁牌坊窝在家等三胖子来挑水的小寡妇。感时花溅泪们是给露珠镶爪托儿自找别扭,看着落樱说俺也一样是都知早晚这回事的无可如何,圣愚光着腚满街跑总算心里没事,节妇烈女一肚子牙和血叫不出屈,情绪问题不分中外,脑袋有包何论东西。
圣愚这特质在中国可对应的是拙朴,是傻人有傻福的变形,这福是出于老天还是上帝并无区别。正如支离疏支离的是肉身而依此支离仍可安立于世间,疯子支离了心智,如何不堪在这自以为是者的世界里被尊王攘夷?所谓神迹往往并不是超自然的力量造成了神迹,而是被理性框住的人们感受到了不可思议,一旦不可思议,马上双膝跪地,于是济公从胳肢窝搓下的泥球就成了治病的良药,乞儿唾口浓痰就让被画皮鬼掏心的爷们儿恢复了生机,可见中国人也爱颠覆脏净与美丑,也爱给不起眼的边缘人赋予点儿逻辑以外的超能力。
都魔怔成这样了他是怎么活下来的——对此有理智的人无法理解。人人都有的感情,带着些许矫情强调一下安上类别就成了独特美学。强行拔高和标签化细分是头脑去认知并归纳世界的方式,也是头脑确保自身存在的方式,于是疯子饿了就捡脏的也吃,而理智者硬是空腹减肥三餐定时,一只鸟说啊看这天杀的小花花真美好就成了物哀,而去码头搞点薯条就成了庸俗粗鄙。自其异者视之,肝胆胡越,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立圣愚与物哀其根源是做作和多事,找同类你可以揪着此特性自己通缉。
——谦儿:这么看,说相声要有意义和相声得先搞笑也在一个层次上没拉开距离,把抽烟喝酒烫头作为个人特色总念叨也没多大意思……哎,我这是不是就算物哀了?
——德纲:所有的突出都来自强调,煎饼摊点红酒喝的是份妖娆,心里苦说不出的只能胡闹,蔫坏人装老实才浅斟低啸,不信问雨花台三十万精魂哪里去了,怀物哀不恤人算哪门子并插菊刀?坑他人逞己欲是有脸不要,听了风就是雨你也沾一身骚。
——谦儿:这一说我明白了,敢情他是把咱们当物,借屠杀体会他们自己的生之哀呢,这欺骗性可太大了。
——德纲:所以你没有物哀,也没有被圣愚。
——谦儿:那我是?
——德纲:你是算五百除二的时候得出一百七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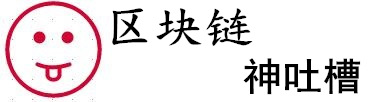 区块链神吐槽
区块链神吐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