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标题:艺术

今年距离二战结束已经70多年了,人类又进入了谁看谁都不顺眼,整天憋着要大打一架的状态。感谢核武器,保证了大方面的和平,距离人类憋的难受到丧心病狂的开始使用核武器的时候,还有一段时间。
现在是全球精神病的时代,除了一些根本性原因,精神病传播能力的迅速增强也是一个重要助推器。自从有了智能手机,原来获取一些亢奋信息还需要找个地方打开电脑,现在不用了,随时随地只要一低头,就可以high起来。低头是一个标志性动作,意味着和周围世界隔绝,进入自己的精神病世界。头一低,颈椎一卡住,丹田与大脑的沟通被阻断,大脑可以随便的妄想。人人都变成霍金那样的人,身体没有作用,就剩一个脑子在狂想。
在石器时代,身体的需求是第一位的,为了实现吃饱就要消耗不少时间。大脑是身体的一部分,帮助身体的整体目标得以实现。现代社会,人的大脑已经反客为主,所有身体各个部分都是臣服于脑海中的狂想。
艺术是个有意思的东西。艺术是一种预言,艺术首先表现了人们的精神世界,然后人们会慢慢在现实中实践自己的精神世界所结出的果子。从这个角度说,艺术是提前写好的历史。
古代的艺术,即使不是很远以前,起码从表面上,还讲究一个均衡全面,这代表着那时候人的精神世界里,有非我的存在,自我是受限制的。近现代艺术的倾向,越来越剥离非我,越来越强调自我的感受。一开始也许是我思故我在,后来思已经不够劲了,一步步发展过来,已经是我疯故我在。如果不疯,人会感受不到自己生命的存在。如果不疯,人会好像悬在一个大虚无当中,好像自己要被虚空吞没。
研究历史的时候,如果仅从经济状况等角度入手,把人看作一个具有理性的经济动物,是非常不够的。经济利益对人的鼓舞和带领,远远低于狂想。真让人着迷的,从来都是fantasy。人们只是需要给自己的fantasy寻找一个经济学上的或者其它某种形式的借口。
仔细观察任何一场狂热,只要开始了,即使运动发展的结果与最初的目标正好相反,狂热也丝毫不受影响。一旦开始,最初的目标就已经完成了使命进了坟墓,剩下的,就是狂热来掌握。

达利的这幅记忆的永恒,是最好的说明。
区块链神吐槽:达利称自己在《记忆的永恒》这幅画中表现了一种由弗洛伊德所揭示的个人梦境与幻觉,是自己不加选择,并且尽可能精密地记下自己的下意识,自己的梦的每一个意念的结果。
一切狂热,都是从打烂现有的权威作为第一步,然后构建自己的想象的世界。世间最大的权威,不是某个组织或者机构,最大的权威就是时间。世间万物,莫不在时间的统治之下。tucaod.com
达利的这幅名作,就是向终极权威---时间,发起了挑战。这是人内心深处的最终极幻想。这幅画创作于1931年,它就如灯塔,预言着现在的人们。
30年代末,开始世界大战,然后诞生了美苏两大权威,确立了世界的秩序。90年代苏联这个权威崩塌,现在,美国也开始要一手毁掉自己建立的战后秩序。自己革自己的命,自己看自己不顺眼。
如果把真正的上古艺术和现代艺术做一个比较:
上古艺术:感动但不冲动;强悍但不疯狂;凶狠但不狂热。
上古艺术很像老虎或者狮子,老虎狮子即使在凶狠的捕猎,头脑也是极为清醒的,一旦势头不对,立刻就会调整,极其理智。
现代艺术核心就是扭曲、摧毁。Fantasy(幻想)。这是人的本来面目。老虎不会有fantasy,人会有。
留给这个世界的,必然是刀。我只是希望能是一把优雅的玉刀。

原文标题:艺术(二)
今天上午发的那一篇里的青铜器,是商代的。多好啊!看整体威风凛凛,但注意看细节,每一个线条,又都极柔软。大的布局很简单,细节又极繁复,但这种繁复又没有一丝一毫的多余。这种以极柔软表达极刚强,以极繁复表达极简单,仅仅这里面的艺术境界,商之后都再也不会有了。对于大布局的极简,后世宋代似乎又活了一下,然而宋代没能脱离情的束缚,宋的艺术,骨子里是诗的升华,终究还是情。商代的东西,是“无情”的,商代的东西是“有意”,商代,无情有意,极柔极刚,极繁极简,这种灿烂的境界,即使留下几件器物,也是远远超过一切其它艺术,更不用提,现代社会的发泄型艺术。现代社会的艺术,连情都不是,只有欲。
前几天看了一段张老道长的讲课视频,老道长讲的是太乙金华宗旨。我听了之后,算是理解了他的修行思路,也是太乙金华宗旨的修行思路。
他们的修行方法的思路就是从人眼前的光入手。后天心思不动的时候,是性光,后天心思一动,就变成了识光(太乙金华宗旨第10章)。“凡人视物,任眼一照去,不及分别,此为,性光,如镜之无心而照也,如水之无心而鉴也。少刻即为“识光”,以其分别也。”金华宗旨的方法,就是抓住性光,性光属先天,他们是从性光开始回光,因为性光源自先天,他顺着性光往回找,就找到先天了。太乙金华宗旨就是这个路子。
所以他入手的地方,是个极其脆弱的东西。人只要心思一动,性光就蜕变识光了,就没法用了。这导致修行人必须得跑到一个极安静极隔绝的场所,不能有任何外部干扰。同时还得做到非常入静,入静越深,性光越大,他越能找回先天。
这个方法,还真是适合出家人来练。一个在家的人,很难有这个条件。
不得不承认,这个方法确实是个方法,下手处不一样,我学的方法是从身体改造下手,把妨碍先天炁出来的身体障碍清除掉,恢复人的本来状态。金华宗旨是从后天中抓住唯一的一丝先天的尾巴,抓住这个尾巴往回找。这个思路,看来和古埃及的荷鲁斯之眼甚是相通。荷鲁斯之眼的特点,就是可以是左眼也可以是右眼,就像金华宗旨强调二目之中是天心一样,既是左眼,也是右眼。我觉得这也是荣格等西方人非常喜欢太乙金华宗旨的原因。
这个修行方法,我自己猜测,来源于印度的可能性应该远大于中国本土。中国上古的东西,并不倾向于突出二目中间的地方。良渚是上古文化中最突出眼睛的文化,即使如此,看良渚的神徽,即使是丹田处,也是一张完整的人脸,也是两个大眼睛,虽然良渚的先民们在雕刻上强调了丹田处双目的相连,但并没有合成一只眼睛。没有类似于荷鲁斯之眼那种可左可右的艺术表现形式,即使在一些小器物上,完整面部的其它地方都被省略了,也是剩下两只眼睛,从没有一只眼睛的现象。可见中国本土上古人的思路。
这两种不同的表现形式,表明了一个根本的分歧点:以性光下手的思路,从一开始就排斥了后天,而中国本土上古的先民,并不认同这一点。比如琮王上的完整神徽,全身都是气旋,意思就是全身都充满先天炁,先后天合一。而古埃及的宗教画像,往往都是以头部的不同表现不同神灵,身体往往只是一个普通的身体,这是一种只重先天排斥后天的价值观。
如果在放眼看一看当今流行的艺术价值观,几乎就是古埃及这个价值观的堕落版。现代人根本没有先天,但又无形中受古埃及的审美观的影响,于是就充斥着伪造的神圣。然后把这个伪造的神圣抬的极高,好像其它的都是更低等级的身体,一旦和这个伪神圣相冲突的,都是应该被灭掉的。
所以,这个世界已经不可能再尊重广泛的共生。只有共同尊重同一个伪神圣的,才能共生。
原文标题:艺术(三)

这是宋徽宗的名作《听琴图》,大概就是君臣三人聚在一起弹琴,中间那个道士打扮的是徽宗。前几天在网上看到了这幅画的细节,很有意思。
先看弹琴的人,注意看他的表情

再看听琴的人,看他的表情

上网去搜一搜现在弹古琴的人,根本见不到这样的表情。在这幅画里,无论是弹琴的还是听琴的,都是那种“有意无情”的状态。显然,音乐,并没有勾动他们的情绪,他们享受音乐,也不是为了心情的抒发。
www.tucaod.com/7653.html
由此说一说我对音乐的理解。
音乐分两部分,一个是音,就是乐器发出的声音,一个是曲调。现代艺术非常重视曲调,有个好的调子有个好的节奏,一首曲子就成功了。现在重视声音本身的越来越少,大概这也是商业化的需要。
我是个俗人,打个俗的比喻,如果把一首曲子比作做饭的话,我认为曲调某种程度上像火候,而声音本身,就像食材。我的厨艺观是,食材本身是主要的,火候虽也重要但要配合食材,以食材特点为基础,不可妄动。同样的,我认为曲调是以声音为基础,不可随便乱调。如果以曲调为目标而搭配声音,属于一种扭曲。
可以看看古人的议论,白居易的《琵琶行》里有一句:“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这里说的非常直白,高手出来,不用曲调,拨几下弦,情就出来了。这就是声音的作用。玩乐器的高手,单纯的仅仅使乐器发声,发出的音就是不一样的,情在音中。这才是音乐。
白居易还有一首诗《废琴》,“丝桐合为琴,中有太古声。古声淡无味,不称今人情”。白居易在这里感慨,以前的琴发出的声淡然无味啊,不合现在人的口味。这也说明,越古老的时候,人们并不追求声音如何催动人,越古老的音,是听起来无味的,不是激动人心,而是纯粹的声音本身。我是这么认为,上古时人们不是为了自己的情绪抒发而去听音乐,他们是在大自然中寻找美妙的声音,这是一种很纯粹的审美,就像朱砂的红色,那种纯粹的红色本身就很美,同样的,美妙的声音本身就很美,没有曲调也很美。
李白有首诗,《听蜀僧濬弹琴》:“蜀僧抱绿绮,西下峨眉峰。为我一挥手,如听万壑松”。这里把演奏者的高超技艺描述的活灵活现,一挥手,万壑松涛就来了。高手对于声音的超凡驾驭能力,真是令人称绝。
回到徽宗的《听琴图》,演奏者和听众的表情,让我想起了王维的诗《竹里馆》:“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这里王维的状态是,弹琴后会长啸的。为何长啸?丹田气满,崩裂而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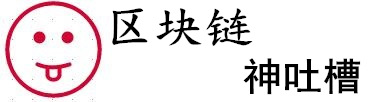 区块链神吐槽
区块链神吐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