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标题:去趟民国 | 陈独秀的个性和人品
悠悠道途上,白发污红尘。
沧溟何辽阔,龙性岂易驯。
陈独秀晚年的这首诗,很能说明他“性狷急不能容人,亦辄不见容于人”的独特的个性。他一生在政治斗争中冲击,雄辩滔滔,最终曲高和寡,形单影只。晚年僻居四川江津,布衣蔬食,贫病交加。昔日的“不羁之马”,虽已是“气尽途绝,行同凡马踣”,但是,这个倔强的老人,依然是独往独来,我行我素,至死不变。
倔强刚烈
陈独秀幼年丧父,祖父陈章旭担当起对他启蒙教育的职责。这位晚清候补知县孤僻古怪,周围邻里的孩子都怕他,背后叫他“白胡爹爹”。他教孙儿读书,纯用传统的灌输法,恨不得七、八岁的小孩,一年内就读完四书五经。同时读书就是背书,而一旦背不出来,祖父就会大打出手。无论祖父怎样毒打,陈独秀总是咬紧牙关,不吭一声,不掉一滴眼泪。白胡老爹气得咬牙切齿,捶胸顿足,气恼而伤感地骂道:“这个小东西,将来长大成人,必定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凶恶强盗,真是家门不幸。”
五四运动爆发后,陈独秀在北京的处境已十分危险,他的几个朋友纷纷来函,催促其迅速南下,暂避锋芒。而他却义愤填膺地回答说:“我脑筋惨痛已极,极盼政府早日捉我下监处死,不欲生存于此恶浊之社会也。”6月8日,他又在《每周评论》上发表文章,称科学研究室和监狱,是世界文明发源地,号召青年们“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他亲自起草《北京市民宣言》,甚至不拘泥于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教授的身份,亲自去公开场所散发。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他连任五届委员长、总书记,他的个性脾气始终不变,和党内同志辩论问题时,总是先声夺人,以势压人,发作起来,动辄拍桌子、砸茶碗。过后,他也知道 “适才的动作是过火了。”中共“一大”代表李达称陈独秀是“恶霸作风”,并不无偏颇地说:“这个家伙要有了权,一定先杀了人以后,再认错。”
中共初创时,共产国际派马林来华,他与陈独秀几次会谈,都没有成功。后来,他让张太雷转告陈独秀,中国共产党必须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陈独秀听后,愤然而起,拍着桌子说:“各国革命有各国情况,我们中国是个生产事业落后的国家,我们要保留独立自主的权力,要有独立自主的做法,我们有多大能力干多大的事,决不让任何人牵着鼻子走,……”说完,陈独秀不顾张太雷的笑脸劝留,拿起皮包,匆匆地走了。
1932年10月,陈独秀等托派头头,几乎全部被国民党中统特务逮捕,在由上海押往南京的途中,他竟“酣睡达旦,若平居无事者然”,其处危不惊,置生死于度外的气节,一时传为佳话。到了南京,国民党军政部长何应钦在会客室传询他,他挥毫题赠:“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传询毕,军政部的青年军人团团围住陈独秀,向他索书纪念。他欣然应允,挥毫题赠这些素昧平生的年轻人,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等,直到墨汁写尽,方才解围。
次年4月,国民党江苏省高等法院公开审讯陈独秀等人的案件, 指控他有“危害民国”的“叛国罪”。闻名全国的大律师、陈独秀的故友章士钊主动当他的辩护律师。章士钊费尽口舌为其辩护。陈独秀听罢,极不满意,竟拍案而起,郑重声明:“章律师之辩护,全系个人之意见,至本人之政治主张,应以本人文件为根据。”使章士钊尴尬难堪。后来,国民党还是以所谓“叛国罪”判处陈独秀13年徒刑,他不服判决,在法庭上大声抗议:“我是叛国民党,不是叛国。”事后,陈独秀的老朋友柏文蔚曾对他的第三个儿子陈松年说:“你父亲老了还是那个脾气,想当英雄豪杰,好多朋友想在法庭上帮他的忙也帮不上。”表示出无可奈何的神情。
抗日战争爆发后,陈独秀的抗战主张同中共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似有共同之处,中共中央向他表示如能承认托派错误,便可考虑联合抗日或回到共产党内来。陈独秀拒绝承认错误,甚至说出了这样的话:“我决计不顾忌偏左偏右,绝对力求偏颇,绝对厌弃中庸之道,绝对不说人云亦云豆腐白菜不痛不痒的话,我愿意说极正确的话,也愿意说极错误的话,绝对不愿说不错又不对的话。”“我不迁就任何人的意见”,“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张,自负责任。……我绝对不怕孤立。”
坦诚爽直
他与朋友相交时披肝沥胆,以诚相待,甚至与初识的朋友,也快人快语,直言不讳。1911年初,他在杭州陆军小学堂任教时,结识了江南著名文人刘季平,并常到刘季平家作客。一天,他在刘家看到贴于壁上的一首署名沈尹默的诗,不禁反复吟哦,并询问刘季平:沈尹默何许人也,家住何处,刘季平(刘三)一一作答。隔日,他找到沈尹默家,尚未进门,便大声地自报家门:“我叫陈仲甫。昨天在刘三家看到你写的诗,诗做得很好,其字俗入骨。”沈尹默听后,颇觉刺耳,心想,我与此公从未谋面,以前曾风闻其名,可不料想第一次见面就当头棒喝,直陈人短。但是仔细一想,他说的也有理,自己的字写得确实不好,此公可谓挚友,交友就应交这样的人。于是,沈、陈订交,时常谈诗论文。沈尹默也从此发愤钻研书法,后来终于成为著名的书法家。
陈独秀1932年被捕后,刘海粟曾赴狱探视。两人久别重逢,分外高兴。刘海粟握着陈独秀的手,连声说:“你伟大,你真伟大……”陈独秀也很兴奋,抢着说:“你伟大,敢于画模特儿,和封建势力斗争……”,接着又大声抗议说:“蒋介石要我反省,我有什么可反省?”两人高谈阔论,旁若无人,狱卒和囚犯无不惊讶。临别时,刘海粟提出要陈独秀题字留念。他不假思索,一挥而就,写的是“行无愧作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以后,他还为刘海粟所画黄山《古松图》题词:
黄山孤山,不孤无孤,孤而不孤;
孤与不孤,各有其境,各有其图。
亚东图书馆的汪原放也曾去探视他,并向他求字,他写了两张,其中一张写的是:“天才贡献于社会者甚大,而社会每迫害天才。成功愈缓愈少者,天才愈大;此人类进步之所以为蚁行而非龙飞。”他对“社会每迫害天才”表示出无奈和抗议,而在无情的命运面前,却又毫不气馁,屡踣屡起,死打硬拼。
“身处艰难气若虹”
本世纪初,陈独秀到芜湖办《安徽俗话报》,寄宿在芜湖中长街科学图书社的楼上,这是一间破旧的楼房。他在这里一天两顿稀粥,而每天的工作总是排得满满的,除了撰稿、编辑外,还要做分发、卷封、付邮等琐碎小事。楼下客厅挂着他书写的对联:“推倒一时豪杰,扩拓万古心胸。”20年后,陈独秀仍然怀念这段清苦艰难的生活经历,他说:“我那时也是二十几岁的少年,为革命感情所趋使,……日夜梦想革新大业。何物臭虫,虽布满吾衣被,亦不自觉。”
中共“一大”后,陈独秀辞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职务,来到上海,走上党的领导岗位。当时,脱产的党务工作者,每月只有30元或40元的生活费,这当然不够陈独秀一家的开销。他几乎每天都给党刊写文章,可那是义务,是领不到稿酬的。他的主要经济来源是亚东图书馆出版的《独秀文存》的版税。每当手头拮据,便来亚东,老朋友相知有素,经理汪孟邹先和他闲聊,然后主动开口问他:“拿一点钱罢!”这时,他点点头,拿走一元或二元,再略坐片时,便走了。亚东图书馆的职员都是安徽人,对他的家境十分了解,每逢此时,总要私下议论:“他家里有钱哩!但是,他不管怎样,再也不要用家里一个钱。他真是一个硬汉子。”
使陈独秀困扰终生的是经济问题,他在亚东图书馆日复一日地支取稿费和版税,早已透支。入狱后,汪原放来探望他,他十分内疚地说:“我欠亚东的钱实在不少,想想心里很难过。我打算将《独秀文存》重印,适之又一再催我写自传,我也着手准备。这样,以版税和书稿抵债,我也略为心安了。”但是,由于陈独秀的政治身份,他的《独秀文存》早已不能登报门售。于是,自传的写作便耽搁下来。
时隔三年多,1937年7月上旬, 《宇宙风》杂志主编陶亢德经汪孟邹荐约,陈独秀开始动笔撰写《实庵自传》,所写内容以能出版为原则,他只写了“没有父亲的孩子”和“江南乡试”二章,即已产生轰动效应,被誉为“传记文学之瑰宝”。不久,陈独秀出狱,他奔走抗日活动,无暇撰写自传。可是,陶亢德却连连催促,他复信一封,指出传记著作不可“草率从事”,“世人粗制滥造,往往日得数千言,弟不能亦不愿也。普通卖文糊口者,无论兴之所至与否,必须按期得若干字,其文自然不足观。……出版家往往不顾著作者之兴趣,此市上坏书之所以充斥,可为长叹者也。”
陈独秀对文字学尤有造诣。1939年,国立编译馆约请他编著教师用的文字学专著,并分两次预支了一万元稿费。他写好《小学识字教本》上编后,即交给编译馆,并嘱先行出版。 “小学”古义为文字学,广义又为语言文字学。就此而言,书名为《小学识字教本》是确切不过的了。可是,时任国民党教育部长的陈立夫怕读者误以为此书是小学生的识字课本,主张去掉“小学”二字。陈独秀认为陈立夫之议纯为多余,坚不应允更改书名。于是,书稿束之高阁,未能出版。至陈独秀逝世,预交的稿费,也遵陈的嘱咐未动一文。
入川后,陈独秀晚境凄苦,他威武不屈、贫贱不移的品格和风范,赢得人们的普遍尊敬,所以人们常主动帮助他。其中以他的学生为主体所组织的“北大同学会”,对他尊如父师,不定期的为他资助生活费。为此,他十分感激,把书稿《古音阴阳入互用例表》和《连语类编》赠给北大,以资报答。亲友知他有“无功不受禄”的脾气,在资助他时,多请他磨墨展纸书写字条、字联、碑文或篆刻金石,以作酬答。陈独秀迫于生活,近乎靠别人施舍度日,这极大地伤害了他孤傲、清高的自尊心。所以,在致谢的复信中,不乏如下字句:“既感且惭”,“且感且愧”,“不胜惶恐之至”,“寄回恐拂盛意,受之实惭感无既,辱在知己,并感谢字亦不敢出口也”,“屡承厚赐,何以报之”等等。
他在四川的最后二年,生活更为窘困,甚至以典当度日。老友柏文蔚赠送给他的灰鼠皮袍被送进当铺,还卖给房东家一些衣物。他和潘兰珍的住房陈旧、简陋。室内两架木床,一张书桌,几条凳子和几个装满书籍的箱子,墙上挂着一张岳飞写的“还我河山”的拓片条幅,令人见了肃然起敬。
陈独秀去世后,老友朱蕴山曾赋诗一首,其中有云:“一瓶一钵蜀西行,久病山中眼塞明;僵死到头终不变,盖棺论定老书生。”他可谓是至死未改清白、清贫的书生本性。
“终身反对派”
1942年1月,陈独秀在给友人的信中说:“自来之论, 喜根据历史现在之事变发展,而不喜空谈主义,更不喜引用前人之言以为立论之前提”,“故而见得孔教道理有不对处,便反对孔教,见得第三国际道理有不对处,便反对它,对第四国际第五国际、第……国际亦然。适之兄说弟是一个‘终身反对派’。实是如此。”他还对友人邓仲纯说过他“一生就会作反对派,从反满清一直到反蒋介石。”他一生由“选学妖孽”转而康党、乱党、共产党,直至托派、终身反对派,不时否定历史、否定自身,“既不厌生,复不畏死”,“相信进化无穷期”,“时间上没有‘万世师表’的圣人,也没有‘推诸万世而皆准’的制度”,“空间上没有包医百病的良方”。对人生对社会始终抱着积极进取、甚至激进偏颇的精神。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共产国际几乎全部诿过于陈独秀,8 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 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将他拒之会外。他与秘书黄文容、汪原放等乘船去上海,一路上脸色铁青,嘴角紧闭,很少说话。难得开口,说的也是反反复复一句话:“中国革命应该由中国人自己来领导。”到了上海,黄文容问他:“仲甫同志,鲍罗廷和中央屡屡让你去苏联学习,你为什么拒绝呢?”陈独秀回答说:“你懂什么?莫斯科让我去学什么啊?学中国革命问题?中国历史是中国人懂得还是外国人懂得?你以为中国问题还要请教外国人,难道外国问题也请教中国人,中国人能懂吗?”共产国际召开第八次执委会时,联共(布)内部的派别斗争已白热化,托洛茨基被开除出党,驱逐出境。此时,陈独秀如去苏联,以他那固执的个性,既不可能说些不痛不痒的话,也不可能不说出些与共产国际、斯大林相悖的言论,他在苏联是吉是凶,何时能回国,都是难以想象的。
陈独秀晚年的某些思想和主张,遭到中国托派的攻击,他毫不留情地予以反击,他说: “这般极左派的人们,口里也说参加抗战,而同时却反对把抗日战争的意义解析得过高,他们的意见或者认为只有反对国民党统治的战争才是革命的”,他揭露说,中国托派已“不是抗日行动,而是在每期机关报上满纸攻击痛骂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文章。”他郑重声明: “我的意见,除陈独秀外,不代表任何人。我要为中国大多数人说话,不愿为任何党派所拘束。”他与中国托派渐行渐远,已基本没有政治的、组织的关系。
1938年3月,长达三年的莫斯科审判结束, 一大批老布尔什维克被处决,斯大林肃反扩大化的错误,造成了恶劣的影响。陈独秀对此极为反感,他对友人说:“现在苏联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专政到反动派,我举双手赞成,但专政到人民,甚至专政到党内,难道是马克思列宁始料所及的吗?此无他,贱视民主之过也。”夕阳残照,年逾花甲的陈独秀自诩“哲人间世出,吐词律以诚。忤众非所忌,坎坷终其生。”他依然不厌其烦地宣传他的政治主张,即通称的“最后的见解”,其中的是是非非,半个世纪来,一直在研究、争论之中,至今尚无定论。
鲁迅曾浅显而深刻地评价过陈独秀,他说:“假如将韬略比做一问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几支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陈独秀正是这样一位“用不着提防”的光明磊落的人。他冲动、奋进,拔山盖势,摧枯拉朽。他在政治斗争和阶级斗争的激流中,不善游泳,缺乏灵活性,又特别厌恶玩弄权术。他也知道他鼓吹一生的政治见解,是“很难得人赞同”的。历史把他推上了政治舞台的重要岗位,但象他这样性格的人并不适宜于担任政治家的角色。他只能在怆凉、孤独中,走完他曲折坎坷的人生旅程。
微信号:价值线
价值线为5000万中产阶级和高净值人群提供大数据时代最新的价值观察和理财选择,分享诗意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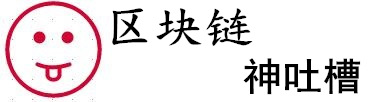 区块链神吐槽
区块链神吐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