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标题:沛县律政江湖
发在《读库2001》上的一篇小文
封建制与郡县制之争
一
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一统天下,自信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功业,决定万象更新。他发明了一个新的称号“皇帝”,并且出台了大量新的制度和政策。
朝会讨论时,大多数新政都顺利一致通过。但有一个问题,却引起激烈的争论。
丞相王绾等提了一个建议:“诸候刚被消灭,原来属于燕国、齐国、楚国的土地,都非常遥远,不在那里封王,就无法稳定当地局势。请把皇帝的几个儿子立为王,希望得到皇帝的许可。”
这句话说了两个问题:
- 这些地区文化上对帝国缺乏认同,发生暴动甚至叛乱的可能性很大;
- 交通、通讯条件决定了,帝国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把力量投放到那里。
所以,分封一个忠于皇帝的国王,给他比郡县长官更大的自主权,算是很有针对性的办法。
何况,让天子的儿子们成为国君,既是古老传统,也符合皇子们的利益。这个建议也算是给各位皇子一个很大的人情。
所以秦始皇把这个提议交给群臣讨论的时候,立刻就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赞同。
但是,廷尉李斯发话了:“当年周朝建立的时候,就采用的这种办法。各国国君开始关系还好,后来亲属关系疏远,就互相攻击像仇人一样,周天子拿他们也没有办法。现在幸亏陛下您英明神武,统一了天下,推行郡县制度,皇子和功臣,只是从国家的税收中取走丰厚的一笔做收入罢了,非常容易管理。天下人都不敢和皇帝有不同看法,这是安定国家的办法。重新分封诸侯,则很不妙。”
这番说辞,既充分总结了历史,又清晰预见了未来,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就又非王绾可比了。
最终,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意见。
这场朝廷辩论,后世的历史书上,往往被称为封建制与郡县制之争,似乎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其实,辩论双方倒都是真心希望帝国能够长治久安。
王绾们更多考虑的是可行性问题:他们显然也不是旧制度的拥趸,主张在赵魏韩推广郡县制,燕齐楚实行封建制,不过是量力而行罢了。
李斯的主张当然更加高瞻远瞩,但要全面推行郡县制,对帝国来说,却存在很大技术障碍。
如果采用分封制,那么一个皇子带着一群大臣,率领一支军队前往自己的封国。
接见一下当地的贵族,要他们表示对自己效忠,一个新的诸侯国也就算建立起来了。
刚被消灭的山东六国里,这些贵族多半有数十甚至几百年的传承,势力根深蒂固。他们未必在乎自己属于哪个国家,所以不久前帝国的大军把他们的祖国灭掉,他们就并没有毁家纾难激烈反抗。现在,当然也不指望他们真心忠于帝国的利益,但只要他们愿意宣誓,然后该缴税的时候由他们去向平民征税,有大规模徭役时则由他们去组织人力,也就可以实现平稳过渡了。
但郡县制就完全不同了。至少县一级的政府,都需要由帝国派遣官吏去进行管理。
- 一方面,这意味着本属于当地贵族的权力,都被帝国剥夺,他们会对帝国产生巨大的抵触情绪;
- 另一方面,帝国一时也很难派遣出这么多官吏。
孝公时代商鞅变法以来,秦国实行严厉的法治。也就是说,政府机构中,需要有大量熟悉法律条文的官吏来完成具体工作,这些官吏被称为“文法吏”或者“文吏”。为了满足这个需求,秦国很快发展出自己独特的教育体系,也就是“以吏为师”,被称为“史子”的年轻人追随资深官吏学习法律和政令,保证了文吏源源不断的供给。
但是,这个一百多年来行之有效的体系,只是为了满足“秦国”这样一个诸侯国运转而设的,要治理“秦朝”这样一个疆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帝国,就显得像往地上泼一杯水,根本无法负载巨大的舰船。实际上,短短十年就摧枯拉朽般把山东六国一扫而空,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全面推广郡县制也是临时做出的决策,事先根本没有人想到要给文吏人才库扩容的问题。
但是大秦体制的最高原则,就是君王的诏旨,符合国情要执行,脱离现实那就创造历史也要执行。既然郡县制已经是既定国策,大秦的天涯海角也不能例外。
无数人的命运将因此改变,在遥远的东方,沛县丰邑人萧何,很快成了因此获益最大的人物之一。
沛县 萧何
二
今天的丰县和沛县是平级的两个县。秦朝的版图中,丰邑是沛县下属的一个乡,而沛县又属于泗水郡(或者叫四川郡)。
秦朝建立之前,出生在这里的刘邦、萧何们的认知里,自己是楚国人。但他们的长辈里则有人记得,几十年前,这里属于宋国。公元前286年,宋国被齐国吞并,但是这里的人没有因此成为齐国人。因为齐国的行为引起了国际公愤,很多国家都冲过来参与瓜分,沛县最终是落入了楚国之手。
因为和魏国相邻,所以沛县受魏国影响也很深。刘邦年轻时代,不事产业,想当游侠,就曾经跑到魏国拜码头,魏国快被秦灭掉时候,魏王假的流亡政府还曾经把丰邑当作都城。
这里的人祖上的情况更加复杂。作为一片有久远历史的土地,要翻老账的话,春秋时代,宋国分化出一个萧国,后来是被楚国灭掉的,萧何是萧国的后代;宋国还吞并过一个曹国,萧何的同事曹参,是曹国的后代。刘邦的祖上,剥离掉神话色彩,大概也可以判断是从西部地区迁徙过来的。
所有这些都很容易导向一个结果:沛县人有乡土观念,但没什么国家意识。对楚国被秦始皇灭掉,他们本没有多大抵触情绪。无非是换一个来收税和征发徭役的主子而已,这个主子是谁,一般人本来就不会太关注。
当然,对于熟悉政府运作的人来说,还是会注意到许多细节差异。楚国的一县之长,称谓上是列国中最尊贵的,采用的是春秋时代国君的称号“公”,所以后来刘邦起兵的时候,也是号称“沛公”。但这位秦朝派来的长官却仅仅叫“县令”或者“县啬夫”而已。当然,更使人惊讶的事,在新的帝国体制下,他的任期如此之短,受到上级的监管却如此之多。想到不需要多久,眼前这位县令就可能调任别处,或者因为过错而被贬谪,沛县父老对他的敬畏,也不免大打折扣。
县令当然也会感知到这一点,但暂时也无可奈何,事实上,他以征服者的身份来到东方,却被告知自己仍不过是领一份俸禄,恐怕也多少有些不满。灭楚的大将王翦曾向皇帝抱怨过,军功再大也终究不得封侯。觉得收益低于预期,可能是统一之初秦人上下普遍的存在心理,只是畏惧严厉的秦法,谁也不敢抱怨说:早知道如此,还不如留着山东六国,隔一段时间打他们一回,可以掠夺战利品,向他们收取子女金帛呢。
但无论如何,县令要赶紧把县廷的行政班子搭建起来。
《史记》这样高屋建瓴的史书,对历史的许多琐屑细节,当然不可能记录。好在由于大量竹简的发现和释读,今天学者对秦代县廷的组织结构,了解也颇不少,不过模糊之处,仍在所难免。
一般推断,作为一县之长的县令,县令最重要的副手县丞,县里最重要的武职县尉,由朝廷直接派遣,也即是秦人。但负责具体工作的文吏,就不能像在秦地那样充分供给,就只能由县令在本地选拔了。
要找到合格的人才实在有诸多困难。山东六国并不像秦这样强调法治,而且他们有自己的律令,现在他们需要从头学习秦国的律法。更糟糕的是,列国文字不同,一捆捆秦法交到他们手上,他们也可能如入云山雾沼,茫然不知所措。
汉代的法律,学童年满十七岁参加司法考试,证明自己能背诵9000个字以上,才能取得为吏的资格。这个规定一般认为就是承袭秦代而来。显然,这是一个需要从娃娃抓起的过程,如湖北云梦睡虎地发现的那位勤勉的官吏喜,据其自述,他进用为“史”时,已然十九岁了。
显然,距离秦国越远的地区,就越缺乏这样的人才。想到自己该怎样凑齐司空曹、金布曹、仓曹、户曹、吏曹、狱曹……那么多部门的工作人员,县令就焦虑得头痛欲裂。
所以当他看见萧何的时候,觉得简直像发现了一个宝藏,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萧何
三
伟大的秦始皇出生于公元前259年,刘邦比他小三岁,生于公元前256年。萧何给人印象是比刘邦略年长几岁。也就是说,公元前221年天下一统的时候,萧何大约年近四旬,早已经错过一个人学习新知识的黄金阶段了。
明确了这一点,再看《史记》里那句似乎平平无奇的评价,才知道含金量有多高:
(萧何)以文无害为沛主吏掾……秦御史监郡者与从事,常辨之。何乃给泗水卒史事,第一。
“文无害”三个字怎么解释,争论很多。有的说是无害就是无敌,文无害就是对法条的理解,已经达到无人可比的水平;也有人说,无害是不伤害别人,文无害是说不但精通法条,而且解释贯彻时又很厚道;还有人说,无害是没有缺陷,所以文无害是精通法条,完成公务达到谁也挑不出毛病的水平。
总是,“文无害”是一个公务人员的极高境界。甚至在整个泗水郡,萧何都拿过行政系统考评第一。
秦国的语言对于萧何来说几乎是一门外语,秦国的法律对萧何来说是一个陌生的体系,中年人萧何是怎么取得这样的成就的?
或者,他确实是语言和法律天才,在极短的时间里就练就了这样的水平;或者,虽然沛县距离秦国很远,也绝不是信息流转的中心,但萧何就是早早预感到秦国将吞并天下,所以青少年时代就利用沛县极其有限的资源,自学了秦国语言和法律。无论哪种可能,他都是一个眼光、才智极其高明的人物。
萧何的公文写作水平如此之高,可以帮助领导年终上计时,拿出一份风光体面的工作报告。这是他的沛县令和中央派来的御史都欣赏他的理由之一,但绝不是全部原因。
我们也可以设想,从秦地远道而来的县令,最大的工作障碍是什么?
他和沛县人语言不通,而且沛县最大的贵族(如果有)虽然已经被列入了打击对象,被责令搬家到帝国的都城咸阳去,但大量的中小家族,一样根深蒂固。县令的工作要想顺利展开,就要解决怎样和他们相处的问题。
对照明清时代的经验,地方官上任之前,会先组建一个和自己一样是外地人的行政班子,处理最核心的政务,来对抗本地人的影响力。但秦代是一个开天辟地以来未有的帝国,还完全不具备这个经验,所以地方官孤立无助的感觉,必然还大大超过明清。
郡县官员的工作繁多,行政、税收、司法、教育……无一不是他的责任。但我们可以把所有这些工作分成两大类:
- 长期任务,是打击地方主义,培养国家认同,让一般黔首都能以萧何为榜样,理解国家的政令;
- 短期目标,则是明面上不要发生大的骚乱,各项考核指标可以完成,尤其是朝廷不断出台的新指示,如修建阿房宫、骊山陵、长城等大工程,需要多少民夫,必须赶紧把人给送过去。
为了完成长期任务,县令需要想方设法打击那些有点势力的家族,比如贯彻商君变法以来的兄弟不析产,则加倍收税的政策,把他们拆分成一个个核心家庭,尽量使黔首原子化;但要实现短期目标,则由于没有其他行政资源可用,反而只有和这些家族搞好关系,让他们愿意配合朝廷的工作。
显然,长期任务无法量化考核,完成不了也问题不大;短期目标一旦有差失,可是立刻丢官罢职的下场。
所谓“明主之法,治吏不治民”,大秦的法令,对官吏比黔首更严厉得多,最艰苦危险屈辱的谪戍,都是优先安排犯错的行政人员去完成的。
所以,该怎么选择,对郡县的长吏们根本不是难题:只有把原有的地方势力先利用起来。
而沛县令要和本地父老的沟通,自然离不开萧何。而萧何这方面的技巧之高,尽管史料有限,我们单是从萧何与刘邦的关系里,也明显感受得到。
萧何刘邦关系
四
刘邦年轻时代是游侠或者说流氓:游和流是近义词;司马迁之前,侠这个字没什么褒义,而氓就是民的意思,也没有太多贬义。所以两个词差别其实不大。
王陵是沛县的“县豪”,刘邦曾经慕名进城,拜过这个大哥;魏国的张耳是享有国际声望的大侠,刘邦曾经跑到魏国城市外黄(今河南民权县),追随张耳好几个月。
这种生活方式,也就是所谓“不事家人生产作业”。但奇怪的是,刘邦三十多岁的时候突然改弦更张,当上了泗水亭长,也就是找了一份体制内颇有点体面的工作。
刘邦的这个转变,基本可以肯定和秦的统一有关。“侠以武犯禁”,是始皇帝推崇的学者韩非的名言;流动人口,自商君变法以来,就是秦国严厉打击的对象。张耳这样的大侠,早早上了帝国的黑名单,只能隐姓埋名流亡,做了“里监门”,也就是社区的保安,被猥琐小吏侮辱,也唯有忍气吞声。
刘邦这样的低阶游侠,不在朝廷的关注范围内,但也不能再跨国游荡,只好回到家乡纳入编户齐民体系,不允许任性的拜码头串联。也就是说,天下分裂,刘邦在国际间流窜也没人视为奇怪;帝国一统,他却反而大受拘束,连从丰邑去趟县城都困难。诚朴的农民可能不太介意活动空间的紧缩,但刘邦不能不感到深深的压抑。
史书上记录了刘太公对刘邦的抱怨,认为这个小儿子远不如他哥刘仲能置办家业。直到刘邦成为大汉皇帝之后,他对父亲的批评还不能释怀。考虑到刘太公自己也喜欢和不良少年厮混,刘邦当游侠混得有点头脸的时候,老爷子大概没什么不满,多半是秦统一之后,刘邦欲当流氓而不可得失业在家,刘太公才有了诸如此类的怨言。
可能也正是这个时候,萧何向刘邦伸出了援助之手:当不了流氓,就来当片儿警吧。
萧何和刘邦都是丰邑人,是最严格意义上的老乡,但两个人的性情和作风完全不同,日常往来并不亲密,不过以萧何的洞察力,很容易发现刘邦身上有一种特别的气质,对社会下层不安分的少年,有强大的感召力,很容易让他们蠢血沸腾。作为政府公务人员,早早笼络住一个潜在的黑社会大佬,总是一笔稳赚不赔的买卖。至于后来实际回报还远远超过预期,那就归根结底是历史进程,非任何人所能预见了。
刘邦还是游侠期间,萧何就多次帮他隐瞒罪行。刘邦成为亭长,则意味着两个人之间有了进一步合作的空间。
和“十里为乡”的“里”指居民点不同,所谓“十里为亭”,这个“里”就是今天说的一里路、两里路的里。亭是治安单位。即在交通要道上,十里设一亭,既负责往来公务人员的接待,又可以维持治安。黑道出身的刘邦担任亭长当然再合适不过,很容易做到必须侦破的案件迅速侦破,一般的违法行为,则被掩盖得不留痕迹。
而萧何此时已经是沛县的“主吏掾”,负责全县重要人事岗位的安排,经常需要和刘邦工作对接。萧何多次表现出对刘邦特别的重视。一个著名的事例是:刘邦到咸阳出差,按惯例同事都要赞助一些路费。别人都赠送了三百钱,只有萧何送了五百钱。刘邦后来的回报是,一个钱十户人家,封萧何为侯时,额外多封了二千户。
沛县主吏掾萧何和泗水亭长刘邦这个组合,和后世影响巨大的小说《水浒传》里,郓城县押司宋江和东溪村保正晁盖的关系非常类似。当然,萧何远比宋江有才能却没有那么大野心,刘邦的眼光智慧胸襟气魄,更非晁盖可比,所以后来两个组合的命运,也大不相同。但一个人坐镇县廷,操控着区域中心的人际关系网络;一个人扎根基层,以秩序维护者的法定身份,经营着黑道势力,然后互通有无彼此配合,甚至不惜担上“血海也似的干系”。
这却是中国古代史上异常稳定的基层权力运作方式。
当然,这类组合运作得越成功,就越意味着沛县令只是一个摆设。有一个人的出现,可能意味着县令不甘心被彻底架空的努力,但结果,这却让他失败得更加彻底。
这个人就是未来吕后的父亲吕公。
吕公为什么看上刘邦
五
《史记》里如此讲述刘邦成为吕公的女婿的故事:
单父(今山东单县)人吕公与沛县县令相友好,为了躲避仇人,做了县令的“客”。
于是,他就追随县令来到了沛县。沛县的“豪桀吏”,即强势的宗族和县廷的官吏,听说县令有这么一位“重客”,都去送礼祝贺。
身为主吏掾的萧何,自然负责具体操办这件事,他命令说:“礼物不满一千钱的,不能进堂就坐。”这时刘邦到了,他一向瞧不上自己这些同僚,就在拜帖上写了“礼钱一万”,但实际上一个铜钱也没带。
吕公看到这个拜帖大惊迎接,见到刘邦的相貌,越发敬重,亲自引刘邦入座。萧何说:“刘季一向爱说大话,办事却不靠谱。”刘邦在大堂上的表现极为放肆,却越发引起吕公的赞赏。所以酒宴结束,吕公就留下刘邦,提出要把女儿嫁给他。
这个故事当然有人视为离奇,由于司马迁写作《史记》的时候,吕氏家族已经作为政治斗争中失败的一方被彻底铲除,太史公对吕家的记录,向来被认为疑点重重。但还是有些毫无造假必要的信息可以信任:比如吕公是县令的“客”。
这个“客”,自然也就是孟尝君“养客三千”的客。意思是吕公从县令那么获得某种收益,而回报则是为县令出谋划策,解决困境。
对照《项羽本纪》,又会发现吕公和沛县令的关系,与项梁与会稽郡守殷通的关系,倒是颇有些相似。
作为楚国的贵族,项氏的封地是项(在今河南沈丘),司马迁又称项羽为下相人(今江苏宿迁),但项梁叔侄后来起兵反秦,是在会稽郡的郡治吴县(今江苏苏州)。
项梁之所以会去吴县,理由和吕公到沛县相同,是逃避仇家。然后项梁显然很得会稽郡守的赏识。“每吴中有大繇役及丧,项梁常为主办”,尤其是能够担当主持大规模徭役的重任,恐怕不仅是因为项梁的才能超过本地的人才,而是郡守更愿意把这个任务交给他。无论如何,郡守对项梁的信任无可怀疑,所以后来决定谋反这样的大事,都是第一时间想到找项梁来商议。
项梁的身份,大约也正是郡守的“客”。
前文已经提及,本地势力不可信任是地方官的基本判断。而后世官员的应对之道,是上任的同时,就要组建一个由外地人组成的行政班子。
明清时代,州县官会聘请若干幕僚作为自己最重要的参谋,至少会有一个负责税收(钱谷),一个负责司法(刑名),他尊称这些幕僚为老师,民间把在衙门工作的各色人等都称为“爷”,这些老师也就是所谓“师爷”。不但如此,重要的具体事务,如看守大门,负责文书签转,看管仓库和打理厨房……也都不能信任由本地人充任的书吏和衙役,所以州县官还会雇佣大量长随,承担这些工作。
师爷和长随都没有公务员身份,他们的收入由地方官自掏腰包支付,只有他们,才和地方官是真正的利益共同体。
秦代的郡县官员面对盘根错节的地方势力,理想中最好的应对策略,当然是任用更多的秦人,但秦人数量远远不够,那不得已而求其次,也要尽量使用外地人。沛县令用单父人吕公,会稽郡守用下相人项梁,遵循的就是这个逻辑。
如此,沛县豪桀吏欢迎吕公的那次宴会,涵义就好像变得复杂起来。本土势力与外来力量高坐一堂谈笑风生,言辞中却只怕闪烁着许多刀光剑影。刘邦以二愣子的形象出现,不仅是瞧不起同事,更明显是对吕公的示威。萧何贬斥刘邦,则确保做到了有礼有力有节,分寸拿捏,极是精妙。
而秦代与明清的差异也立刻显示出来。幕友和长随本身都不拥有什么资源,背叛地方官勾结本地势力得不偿失。吕公却是豪家,项梁更是贵族,对沛县令或会稽守并没有那么强的依附性;单父和沛是邻县,下相和吴都是楚地(不管今天的宿迁和苏州关系如何,那时并没有大内斗省的观念),更容易建立彼此认同,尤其是面对人憎鬼嫌的“秦人”的时候。
所以,他们都选择了抛弃地方官而与本地势力相结合。
- 项梁赢得了江东父老的信任,在郡守满心期待和他谋划造反事宜时,喊来项羽一剑砍掉了郡守的脑袋;
- 而吕公那个本来据说可以成为县令夫人的女儿,则嫁给了泗水亭长刘邦。
刘邦造反
六
萧何有一个特别值得夸耀的成就:就是朝廷到泗水郡来视察工作的御史,对他特别欣赏,以至于想把他调到中央去工作。
萧何很感动,然后拒绝了他。——众所周知,拒绝是比接受更加荣耀的选择。
萧何为什么会拒绝这样的好运呢?当然不会是淡泊名利。分析萧何的心理:
- 往浅了说,是他知道秦朝只是秦人的秦朝,自己一个东方人到咸阳去,也不会有多少发展前景,反而失去了地方上的丰富资源;
- 往深了说,萧何也可能有这样的远见:他知道秦朝不会长久了。
毕竟,在县廷工作能接触到许多机密的人,比任何人更容易体会到这个政权的病魔缠身罪孽深重。
秦朝的制度,不管你喜不喜欢,它代表着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这个没有问题;秦始皇是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的千古一帝,这个也没有问题。
这些年读到不少文章,喜欢论证秦始皇道德高尚心地纯良所有的政策出发点都是好的。虽然这种热衷洗白作风十分儒家,始皇帝大概不屑一顾;引用几根秦简上的动人说辞,就相信史书上记录的暴政都不存在,我也不知道和捡几张六七十年代的《人民日报》,就否认连历史教科书上也认真检讨的事实有什么区别,但谁要坚持认为秦始皇是个好人,也一样不必反对。
帝王的动机好坏,本来就无关紧要,反正这都不影响大秦统治下民不聊生也官不聊生的事实。
这里先要辨析一个数字问题。
范文澜先生的《中国通史简编》里面,罗列了秦始皇时代有哪些大工程,分别征发了多少民夫。范先生把这些人数一加,再除以他估算的人口数,得出结论:“占总人口百分之十五。使用民力如此巨大急促,实非民力所能胜任。”
今天仍然经常可以看到人在引用这个数字。但实际上,15%是这个比例,既高估了,也低估了。
葛剑雄先生提供了更令人信服的分析:范文澜算出来的征发民夫数,高了,因为很多工程并不是同时进行的;而他估算的总人口数则低了。这么算下来:始皇帝的征发人口数,只占总人口的2.5%而已。
但是,这只是直接征发的数量。农业社会和现代相比,最大的区别就是社会动员成本高到骇人听闻的地步。要支撑这2.5%的人流动和服役,以当时的后勤能力,秦朝至少需要动员全国50%的人口。
后来的研究,大概是在葛剑雄先生这个判断的基础进一步细化。总之毫无疑问的是,超过50%的秦朝人被卷入了无休止的折腾之中。
伟大的始皇帝主观上可能确实没想过把社会伤害得如此之深。他所继承的所谓“六世之余烈”“四世有胜”之类,都只是一个诸侯国的经验。征发人数变多,征发路程变远,这个成本是指数增长的,始皇帝按线性增长计算了(毕竟如大家所见,二千年后的历史学家还经常犯这个错误)。皇帝在完全错误的基础上制定了国家发展规划,大秦的官僚系统虽然很快意识到这一点,但面对一个“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的帝王,没有谁活腻味了敢去劝谏送死。
于是全社会民众的生活,就只能被推入万丈深渊。这口大锅,真不是秦二世、赵高等几个小人背得起的。.
《史记》记录得很清楚,刘邦成为盗匪,就发生在秦始皇末期而不是秦二世时代。刘邦解送一批民夫去修骊山陵墓,中途许多民夫逃走,刘邦就干脆选择做了逃亡者的领袖,上了芒砀山。
这部分叙述里有些渲染刘邦是天命所归的神异内容,可以不必理会。但肯定的是,刘邦的家人并没有受到多大牵累。胆敢对刘邦的妻子吕雉不敬的官吏,立刻就被刘邦的小弟击伤,之后吕雉仍然有活动自由,甚至到芒砀山与刘邦团聚过。可能是山野中夫妻相会反而异常兴奋,未来的汉惠帝刘盈,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怀上的。
也就是说,刘邦上山成为盗匪,沛县令根本没有追究。想想也是,他怎么追究呢?刘邦的老丈人是自己的“客”,萧何、曹参为代表的全县官吏,都和刘邦关系密切。他根本凑不齐抓捕刘邦的足够人力。而且萧何一定会提醒他,即使抓住了又怎么样呢?审问追究下来,沛县令注定会把自己卷进去。想到秦法中的各种严苛刑罚,沛县令不能不不寒而栗。
于是繁如秋荼密如凝脂的秦法,只能做一个高高在上的摆设,认真落实执行只会害人害己。这个道理今天研究出土秦简的学者也许有人不明白,但当时的官吏,一定是明白的。
秦朝为什么灭亡
七
读史时经常不能不的承认,只要既得利益阶层团结而能干,很多时候哪怕民怨沸腾,也无可奈何。
而秦帝国的脆弱在于,它实际上没有一个像样的既得利益阶层。恰恰相反,除掉皇帝高高在上,秦代是一个几乎所有人都觉得自己是受害者的时代。
统一之前,秦国的军民觉得发动战争斩下头颅获得军功,是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实现阶层跃升的(当然程度如何极有争议)。如韩非子分析的那样,其实早秦始皇之前,秦国已经具备了灭掉六国的实力,但是却屡屡错失了机遇。韩非把这归结为谋臣不忠。实际上,却未必不是理性选择:留着富庶而衰弱的六国,可以保障打劫的收益而避免管理的成本。
但随着六国覆灭,这条路径反而断绝了。如果不能创造新的治国方式,这就像一只猛兽吃光了所有其它动物,自己也只剩饿死一途了。
始皇帝又相继发动对匈奴和百越的战争,这些新对手的特点是战斗力强劲,而生活极端贫困。换言之,战争胜利付出的代价极为高昂,眼前的获益却微乎其微。开疆拓土满足了帝王的雄心,也确实堪称功在千秋,然而一般秦军将士,只知道自己不能从中分享到什么好处。
至于被派遣到各地的官吏,感受则是到手的俸禄不过如此,朝廷不断交给自己无比艰巨的任务,稍有差失就要受到严厉的惩处。就拿沛县令来说,刘邦叛逃之后他无力将之逮捕归案,这件事他只能瞒一时是一时,之后的日子他一定在担惊受怕中度过。终于有一天,大泽乡陈胜、吴广揭竿而起的讯息传来,那时他的感受,大约不是痛恨反贼而是如释重负,终于有一件事让自己的过失显得不那么严重了。
后人读史很容易注意到的:秦朝郡县的长吏,尽管他们本是秦人,但抛弃这个政权没有什么心理障碍。沛县令、会稽守都是想造反却被刘邦、项羽清理出了革命队伍,后来刘邦伐秦西征的途中,许多秦朝地方官望风开城投降。当然更加至关重要的,一支南征的秦军,选择封锁归途,不理会中原逐鹿,开创自己的世界去了。
六国贵族当然是秦帝国的受害者。顺带一提:这些年来流行的论调里,最荒谬的是:秦之所以灭亡,是因为六国贵族的复辟欲望。这个说法不但大大高估了这些猥琐贵族的爱国热情,更极度侮辱秦始皇的智商:这等于说他一统天下后十多年来,那么多打击贵族的措施竟全然无效,最后被人家一举反杀。
实际上,打击了六国贵族这个目标相当程度是实现了的。所以天下大乱豪杰蜂起的时代,最有行动力的没几个是贵族。即使如楚国的项氏,也是最近几十年战争中崛起的新贵,远不如屈、昭、景等老牌贵族值得夸耀;齐国能和项羽对抗的那几个田氏,虽然是王族,但血统已经不知道疏远到哪里去了(血统比较过硬的田假则迅速出局);张良的家族号称在韩国五世为相,但在战国史料中却不怎么找得到他们活动的痕迹,不能排除只是自我标榜的可能。
在反秦战争最不利的阶段,有分析认为失败是反叛者血统太卑微的缘故,于是有一批贵族被抬出来以壮声色。但灭掉秦朝之后,这些贵族大多又像当时用来擦屁股的竹签一样,被随手抛弃了。
说起来,倒恰恰是萧何这样的官吏,应该算秦朝建立的受益者,但是他们自己却不会承认。
正是因为打击了六国贵族,又没法提供足够多秦国自己的令史文吏,秦帝国创造了一个权力真空,这才给了萧何们上升空间。
类似的还有陈胜、吴广,不管陈胜出身是否是贵族,他早已经沦为雇农,但起义时的身份是“屯长”,那支戍守渔阳的队伍的中层干部,就是说,秦朝建立后,他的社会地位其实颇有改善。
没有秦朝,这些人会被大贵族牢牢压制,说一句“苟富贵,勿相忘”就会招致群嘲。是秦帝国赋予他们特权地位,传授给他们政府和军队的组织管理经验。后来萧何进咸阳,第一件事就去“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可见他也深知这种资源有多么重要。
然而,他们都对秦朝不会有任何感情。这种得益于时代潮流的改善,人更容易倾向认为是个人奋斗的结果。何况小特权要被大特权霸凌,在政府或军队工作中,每天相处的那个骄奢无能的人,仅仅因为是个“赳赳老秦”(姑且借用这个当代人发明的词)就是我的领导,没什么比此类事实,更容易埋下仇恨的种子。可以想象,陈胜吴广斩杀秦都尉,项羽斩杀会稽守,沛县父老斩杀沛县令,得手时一定充满“出了老子胸中多年一口鸟气”的快意。
也就是说短短十来年的时间里,秦在六国故地培养了一个既依托秦的体制习得行政能力和组织经验,获取或政治和社会资源,又对帝国毫无忠诚的阶层。这些人成为反秦斗争中,真正的骨干力量。
一个能够做到让所有人都觉得自己是受害者的帝国,无论看起来多么光鲜威猛,早已注定只是一个空洞的躯壳。
最后抄录一则逸闻,“2018年4月6日,山东滨州狂风大作,高达18.90米、巍峨屹立的秦始皇铜像,在狂风助力下,腾空而起,飞出数十米,龙颜尽失,面目全非。”从网上流传的照片可以看出,这尊号称全世界最大的始皇帝像只是一个空壳,如此说来,倒是没有比这更好的关于秦帝国的象征物了。
微博原文地址:https://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580637955719257
猴子先生田坤:多层奴隶制度里最底层的农业奴隶,经历春秋战国变革,遇到了列国推行小农编户制度,才发现做了国家的奴隶尚不如做封君和商人的仆隶,吏是他们头上新悬的剑。当时民如流水,水土流失,四处逃窜,国家打击商业(减少流动),推行吏治(控制节点),连坐株连(触手深入),终于找到了治民的笊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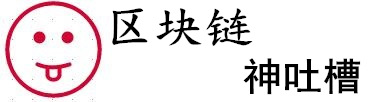 区块链神吐槽
区块链神吐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