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青画作评价
本地画院的老先生来家中做客,适逢我正整理着陈丹青去年展览时的照片,便顺口问及他对陈丹青作品的看法。
老先生修养很好,语气平缓温和,但话锋却含鄙薄之意,他说:
年青人还是少看陈丹青的画,没太多营养。
绘画是一门以技巧为核心的艺术,陈虽旅居美国多年,但画技上并没有明显的突破,甚至是退步的。你相机中他以“画册”为题材画成的静物写生,依我看是他为自己早已过时的画技,找到了一个临摹经典的理由,是小聪明。其中用油画工具画中国传统水墨,更毫无新意,是江郎才尽后挤出的廉价创造力。
我能理解老先生的立场,同时也意识到他的对陈丹青的解读是极片面的,谈话间曾几欲争辩,但出于尊重,旋之默然。
绘画的真正核心,无关于画技的进步,画史每有大突破,其实起始于画家观看方式的递变。
如乔托看到了身旁的驴和远处群山间的透视关系,芬奇觉察出人脸在不同天气下微妙的变化,莫奈注意到早晨六点钟的太阳,塞尚捕捉了苹果的边缘,而陈丹青则发现了绘画原作经印刷技术消解后,制成的画册。
法兰克福学派本雅明在《机器复制时代的艺术》一书中很早就曾预言,随着复制技术的进步,大量印刷品将无法避免地摧毁掉原作中的“原真性”,以及被他称之为‘Aura’的那种东西。
但我通读后发现,本氏之言虽深刻,可还是囿限在了形而上的理论抽象中。他对所谓“原真性”和‘Aura’的定义,其实更偏重社会学、传播学的概念,即印刷品对原作的神圣性、社会功能和意识形态的消解。
而在形而下的物质层面,他似乎并未提及印刷品对原作在色彩的纯度、灰度、明度,以及视觉比例上的强烈消解。
原因或许也很简单,本氏只是高明的理论家,不是高明的画家,他不会画画。
我曾一直感念,在我刚进入时装行业时,就被业内某非常具有影响力的工作室录用。
这个工作室至今保留着一项可贵的传统,即在拟定出新季的用色后,会向巴黎当地的美术馆申请,直接将古典绘画原作中提取的颜色印诸于布疋,尔后裁剪成衣。
我尝试着在画册上,提取与原作相同区域的颜色进行比对。
- 几度试验后发现,当分别从两种媒介中提取的同一颜色,小范围缩印在巴掌大的料块上时,两者间并没有明显的差异;
- 但当它们真正印为成品的布疋,当两份料作大规模的铺开在眼前时,良性的悖论于焉显现。
由于从画册翻印的颜色在经历了纸张差异、像素限制、显示器色差、肉眼校对等一系列无法避免的轻微误差后,它所呈现出的饱和度、灰度、光感层次,都无法企及原作直取的颜色。
这种种细微误差叠加后所产生的轻微质变,甚至会使料作表面会出现一种板涩而清虚的薄雾状光层,真味尽失。
这种官能上的微妙差异很难用语言去准确描述,且涉及到人类的视锥细胞在处理色彩逻辑时复杂的生物学解释,以我的无知,不赘说。
但我发现这种差异其实很像文学诗歌中“原作”与“译本”的差异;
有长期阅读经验的读者可能都会发现,很多诗歌是无法被准确翻译的。
某些高层次的文本,在转换为另一种语言逻辑后,都会丢失掉原始语境中某种极微妙的形韵。这些形韵是高于语言本身而存在的,当它们凝聚成一套既有美学之后,很难进行跨语种的嫁接。
弗洛斯特直言:所谓诗,就是翻译之后失去的东西。
博尔赫斯对历代诗歌进行理论分析时,曾引意大利语中的双关词谚语对此现象详加胪述:
- Traduttore traditore (译者,叛徒也)
- 木心则更残忍地揭露:翻译对诗来说,是谋杀。
艺术和文学于今日的命根子,不在作者的知识、技巧、教养,而在他能把自己手中“创作材料”的“物性”,激发到如何的极限。
早前,绘画中的“颜料”只是叙述性的工具,画家们借“颜料”来试图画清种种物像。
照德库宁的说法是: “油画颜料之所以被发明,就是为了画人的皮肉。”
可自梵·高与塞尚起,他们半自觉地意识到,“颜料”作为一种物质,本身就具有美感。它可以不再服务于被画的对象,而画中的对象,或许只是为了成全画家本人把玩颜料的快感。
我甚至觉得梵·高在最高意义上不是画家,而是雕塑家。
他笔触间的量感、厚薄、以及颜料凝结后的体积感,在小范围的画布上形成了统治级的爆发力。他借向日葵、麦田等一众虚像,俨然为自己进行了一场性格的写生。
近乎同时期,西方的文学、音乐等领域的创作者们都开始注意到自己手中媒材的“物性”。
马拉美将“字”、“词”、“段落”、“标点”、“空白”,这些原本构成诗歌最基础的媒材加以解构,蓄意颠覆了法语语法中亘古不变的线性叙述规则。
兰波一反语言刻画物像的诗歌传统,转而推敲“字”与“词”间的节奏感,并借这种节奏的起伏来阐发人心内的矛盾和冲突。
德彪西则看透古典传统赋予“音符”或理论性或功能性的佯装,兀自调理起“音符”本身。这种对“音符”持续地提炼所引申出的模糊调性,几乎瓦解了十九世纪之前所有的和声体系。
上述种种创作主语间的切换,反客为主的勾当,无意间改变了文学艺术与创作媒材逾千年来的从属关系,并意外催生了立体派、野兽派等巨擘彬彬接踵至,更开新文学之习尚。
可一旦在画布上凸起的颜料转印为照片,“三维的立体”旋即降至到“二维的平面”,无数颜料交融后的细节被轻松溶解。
字词间形韵的不可译性,也让“诗”承托着一种只能生于母国并死于母国的天然悲剧感。
是复制技术的欠发达?还是笔者与译者才智间的差距?—— 或许都是,都不尽是,最终难逃于文学艺术自身的森严律令:媒材物性的难以复制。
而这种当媒材试图跨越媒介所暴露出的局限性,却正是陈丹青创作的药引。
我愿提醒阅者眼目的是,陈氏笔下的野心绝非是为临摹古典先师的原作,而是借众先师的笔意,还原那个他所看到的,被吞噬了无数细节后转印在画册上的原作“遗像”。
他以写实的“实”界定了画册的“虚”,又将精准俘获的“虚”诚实画出,反证了写实的“实”。
此画境不尤让我想起玛格里特于上个世纪的诸般尝试。这位超现实主义者终身使用传统二维绘画,力图揭发人类三维世界中的种种悖论与骗局,他挥起画笔,宣告哲学侵入绘画。
今天看,马格里特还是直捷的,说教性大于绘画性,是一名哲学家在仓促地扮演着一名画家。
他的仓促使后人至今仍停留在对他图示的解读上,从而忽略了画家运笔、敷色等本职技巧的探讨。
而陈丹青则没有僭越画家身份的本体规界。他以精雅的笔触将物象置身于一种不求解读的诉求感,这些单纯到只是“静物写生”的作品看似没有强烈的情绪冲突,其实却是他将几种冲突要素潜心调和后,达成的某种对峙性平衡。这“平衡”所带来的巨大迷惑性,也成功隐去了他身后的哲学大立场。
马格里特以烟斗向世人提问,你是相信图像还是相信语言?陈丹青则对观者诘诘发难,你看到的到底是原作还是画册?
如果说眼见为实,这些作品却旨在忠实还原复制技术所招引来的清虚感。可如果说眼见为虚,它们又是实实在在的后现代实物写生。
所谓画中有画,局中藏局,国人精擅的那套非实即虚的“辩证哲学”在这画册写生的面前轰然崩溃。黑格尔若能亲见这些作品,谅必哑口无言。
自十九世纪起,传统架上绘画因摄影术的崛起逐步边缘化。摄影号称可再现一切物像的能力使“线条”、“阴影”、“透视”,这些凝结了数代画家心力总结出的词汇倍感徒劳。诡谲的是,摄影术至今无法准确再现它转世投胎的前生———传统架上绘画。
陈丹青在精翫这视觉悖论的同时,也带出了他的本土性,作为一名油画家对目下国情的体悟;
他深知画册在西方本作为一种辅助性工具,与挂在美术馆的原作相辅相成的共生关系。但当国中大多数的艺术家、艺术从业者想习知油画的内在章法,国内却无法找到一座世界性馆藏的油画美术馆时,只能以画册来填补眼界的缺失。当这种被画册单向驯养出的眼界开始反哺创作,不堪设想的局面则是可堪设想的。
相传佛陀讲法,以手指月。
其意旨真理如天上的明月,愚僧却紧盯佛陀的手指,认定真理寄存于佛陀指间。陈氏的苦心,莫不为揭露画册如佛陀手指般的工具性,一种对误读的尝试修正。
当代艺术家,如果足够敏感,且诚实,都会承认我们早已置身于影像的世纪。传统架上绘画作为一套“过时”的语言系统,除把玩着自身微弱的内在可能性以外,很难再拓展出新的美学建构,它不再是物化视觉现实的唯一手段,绘画曾绵衍千年的“言说功能”,于今日已渐式微。
陈丹青在如此艰深的语境中,还是捕获了自己的题材。他明知“架上绘画已死”是句残忍的实话,但依然以这套“过时”的语言系统维护着绘画“言说”的可能。
我在观展时曾极短暂地掠过一念:“绘画回来了!”,但旋即清醒,意识到这只是写实绘画绘到穷途时的一缕回光,是绘画“言说功能”的棺柩上,最后一捧土。






幸福塔罗宝月月:某种意义上 绘画史是人类的意识进程史…观察的精微即是意识的精微!技法是有尽头的 技法只是内在拓展的工具之一!陈丹青老师解构了自己 这是哲学层面的重建 是新生。
何索斯基:媒介变更导致的“本真性”和“灵韵”消失可以说是祛古典绘画之魅,陈拿起画笔作成画册是想凭一己之力给当下下被无数复制品稀释掉“本真性”的作品返魅、招魂。个体对抗数码时代,画家之手对抗科技。
晝戌:“招魂”这词用得好啊。
泡泡袖灯笼裤:能看懂一些,看不懂一些,觉得你一直以来的的叙述方式、文字语调,像时光深处凝结成的琥珀,隔绝了现代用语的轻浮,干净、准确、直击云雾笼罩下的真相,通过一层层递进的思维涟漪,和慎之又慎的选词,中文在你这里变得很好看,它下沉,下沉到安静幽微,最值得我们凝视的地方。
一头萌鹿:所以我很警惕太显露个人风格的译者,风格可以留在自己的作品里。本来翻译就容易流失,中规中矩的直板或许还能有想象原作的空间,但刻意展现个人或者呈现一种风格,就像再化妆,更看不清原样了。
佩佩_LPP:简而言之能不能说这是古典艺术和当代艺术的解读和创作差异,以画面为服务到审视每一个工具或者每一个对象本身。
晝戌:是的,相机没有发明前,绘画的很大一部分功能就是“记录”,所以重技巧,因为要精准的还原对象本身。相机发明后,绘画的记录功能被取代,绘画于是和自己玩。发展到后现代,一流画家可以说都不是在画“画”,而是在画对“画”的立场,技巧至多只是辅助。
重返地上乐园:绘画原作与画册的关系,跟原诗与译诗的关系,应该不是一回事儿,除非这里说的译诗指的是机翻,否则,任何译诗都不同程度地算是一种创作,即使水平再差,译的诗与原诗一样,都是创作者生命的产物,毕竟,译作的命也是命啊……
晝戌:我的侧重点在于翻译如同印刷技术一样,都可以不同程度地消解掉原作的细节。
虎掰掰:陈老师也调侃说自己的画没什么价值,这话自嘲可以,别人批评起来还是有些刺耳。不过陈老师的美育贡献,或者称为“给具备一定绘画功底的人提供的思考营养”,这个价值于当代是无人能及的。
黄不忌:我往常把这种艺术“原真性”的缺失——艺术在转呈中某种况味的流失——理解为“通感”状态变化所致。即艺术在直呈时,人的六识六触被多重影响,驱动交互,而转呈时只能通过某一二种媒介,这些媒介又往往专于某个器官的体验,故而原本立体、交互、多维度的感知,就被阉割掉了许多潜藏的东西。
评价李云迪
群友野驴:比如说梁祝吧,就只有俞丽拿,其他都不对。因为她懂越剧,还有小提琴。
我听肖邦的《辉煌波罗耐兹舞曲》,听了超过10个人演奏,就李云迪的最好。只有李云迪的有那种濡慕之情,别的人都没有。通常只有中国人或者被压迫的民族的那种人,那种至性至情的,才有那种感情(比如韩红的天路,一条大河波浪宽那种)。别的人,技巧通天,也没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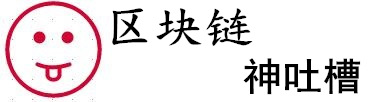 区块链神吐槽
区块链神吐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