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生:改革开放40年 从姓社姓资看企业家与营商环境
华生,著名经济学家
——12月8日2018中国企业家高峰论坛发言实录
很高兴来参加这个高峰论坛。今天恰好是12月8日,这使我想起52年前文化大革命开始的1966年的今天,那年我13岁。由于不能参加当时的免费乘车大串联,后来被获准可以步行串联。于是我就打了个小背包与几个农村中学的同伴从江苏出发,20多天后走到通县。大家在一个大礼堂的板凳上睡了一夜,12月8日裹着散落的稻草和一身虱子沿东长安街走进了北京,当天就被安排住进了新街口副食品厂接待站,以后每天早上吃上了免费的面包和火烧饼。这样,虽然没有赶上毛主席检阅,却并没有减低我的激动兴奋和渴望加入革命历史洪流的热情。

12年后的1978年即40年前的今天,我刚被补录进大学不足一月,兴奋的却又是我的第一篇关于经济改革的文章即将在《南京大学学报》下一期上发表。以此看来个人其实只是时代的产物。倘若生活在不同的时代,我这个人就会有完全不同的命运,成为完全不同的自我。我们生活在父辈和祖先们无与伦比的改革开放时代,才有我们的今天,才有今天的我们。企业家就更不用说了,40年前不用说没有企业家,连个体户都被消灭光了。
因此,无论在这个时代我们作为个人有多少自己的艰辛委屈,有多少遗憾不平,我们真该致敬这40年伟大的改革开放时代!
下面我讲三个问题。
一、姓社姓资的争论再起说明了什么
这一段时间以来,民营经济的地位问题成了热议的话题,而且剧情出现了幸运的大反转。在似乎风平浪静之后,倒是需要我们认真反思的时候。
风波起源于所有制歧视,说私有经济已经完成历史使命,应当退出云云。根子里还是说社会主义是公有制经济,私有经济先天出身不好,应当防范引导、限制乃至消灭。我们长期以来,也是一直强调做大做强国有企业,强调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和共产党执政的重要经济基础和执政基础。这样也使一些人产生了私有和其他所有制经济是异己力量的感觉和印象。对此,邓小平当年的办法是不争论,因为一争论就耽误事,要用是否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社会主义综合国力增强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去衡量,让时间和实践去回答。
大家知道,中国40年前的改革开放是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解放运动开始的。那么40年的实践检验说明了什么呢?非公的民营经济现已占据中国经济超过半壁江山,中国从一个落后的穷国变为世界瞩目的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国家实力空前强大,大多数人从吃不饱穿不暖到今天普遍的小康生活,完全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所以9月份在关于私有经济的流言四起时,我在提交的智库报告中指出,“如果笼统地说公有制是共产党执政的经济基础,那么,公有制越扩大非公有制越缩小乃至消灭,党执政的经济基础就越巩固、越雄厚。那改革开放前单一公有制时我们的经济基础最牢固,而改革开放40年后的今天反而空前虚弱了,这当然是很荒谬的。实际上,如果我们今天真去消灭非公有制经济,就会根本性地动摇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基础和党的执政基础,造成党的事业难以弥补的重大挫折”。因此,今天我们面临的问题不是当强大的国家机器还存在时,如何消灭私有及非公经济,那样只会制造灾难,而是如何与时俱进地变革创新我们的传统所有制理论。
实际上,在有了中国改革开放40年经验的基础上,今天已经可以从不争论到在理论上旗帜鲜明地说清楚了。传统的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经济已经被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所突破和超越。现在我们实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也必须以多种所有制为基础。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并不必也不需要表现在其比例和数量上,而且要采取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实现形式。竞争中性和所有制中立,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也是中国融入全球化市场的通行证。一些人在姓社姓资问题上走不出来,其根本问题是没有认清社会主义的本质,混淆了手段和目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本质是消灭压迫剥削和特权,达到共同富裕和人人平等,当时在理论上设想消灭市场经济、实行公有制和国家消亡只是有助于实现这个目标的手段。
当然有人会说,私有经济的发展不是正造成贫富差距吗?不错,看看财富榜上首富们的巨额财富,确实令人羡慕妒忌恨。他们的一个小目标,也常常令普通人绝望气馁。特别是市场经济中的富裕,确实并不总是靠努力、天赋或者勤奋,而在一定程度上靠机会和幸运,甚至有时也不排斥阴谋和伎俩。但是,谁又能否认,正是这少数幸运而又不乏自己奋发努力、家庭背景与普通人一样的成功人士,激励了千千万万的人去创新创业,诱导了亿万资金流入了创新创业创造财富的洪流,从而做大了整个社会的蛋糕,在不同程度上提高了几乎每一个人的生活水平?要知道,历史上所有付出巨大社会代价的均贫富努力,并没有带来普遍富裕,相反却总是以普遍贫困而告终。
从根本上说,这是因为物竞天择是所有生命体包括动物和人类社会的铁律。竞争是从最小到最大的一切已知生命体的基本生存和发展方式。而竞争就有差距,就有胜出者。试想,如果不论社会上每个人如何努力,都会有或被安排得到同样的结果,都享有同等待遇,那么,无论是社会上的哪个行业或哪个人,还会有人努力吗?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差别就没有竞争和努力的动力。结果的不同和差距是激励努力的必要条件。现代人类之所以能够从动物界包括猿人和众多古人类种属中脱颖而出,今天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让地球上更多的生物和自然资源为自己所用,就是因为其为自己创建了竞争的规则,包括市场竞争的规则。而市场交换的完全自愿性、价格竞争的信息效率使得市场在人类物质生活的领域内,成为迄今最公平和最有效率的竞争方式。
而且,即便在非物质的精神领域,人类也创造出职位、等级、荣誉、名次与奖项,人为构造出竞争的环境,从而推动人类精神、文化、艺术、体育和科学技术等各领域的创造和繁荣。我把科学放在最后,是因为在人类社会早期以万年计的漫长世纪中,人们对自然认识的进步极其缓慢。人类长期在世世代代中只有图腾、幻想和神话而无科学。人类正是靠自己为生存而群居组成的社会,在人际交往的竞争和协作中的刺激和反馈,不断发育和积累了自己的脑力智力,从而最终推动了人类对自然的认识,导致了自然科学的诞生发展。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早期猿人在自然界中的动物性生存技能是靠基因和本能,而在社会交往中的竞争和协作才是推动古人类转化为现代人的关键。因此,人类文明的进步不在于消灭竞争,实现均贫富和人人相同的结果,而在于发展更公平的竞争规则和保护竞争中落败和落后者的基本权利,守住弱者基本人权的底线,以使他们或其后代能够有继续参与竞争的公平机会。
再进一步看,中国今天的贫富差距是全部或主要由私有经济造成的吗?其实并不然。中国今天贫富差距确实很大,按照官方统计基尼系数也在0.47左右。民间将遗漏的未统计进去的隐性财富估算进去,还要高出不少。而且即使按照官方公布的统计数据,我们的贫富差距在全球主要国家中都是属最大之列,更是远远高于东亚成功现代化的日本的0.32, 韩国的0.31 等水平。日本韩国实行的是以私有企业为主体的市场经济,大企业、大富豪也不少,人家的贫富差距比我们小得多,从结果上看似乎更“社会主义”。我们有那么大比重的公有经济成份,贫富差距比人家还大这么多,这是非常值得我们反思的。这充分说明手段不等于目标的实现。
再从构成上看,就更清楚了。公有制在理论上应当大家平等地都有一份。这是从500年前空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产生之时,人们就那么向往公有制的原因。但公有制也好,没有那么多公有制但也不得不有巨大国家机器的世界上其他包括发达国家也好,凡有公共财产、公共事务就得有掌权掌勺的人。在市场难以发挥作用而需要集体决策的领域(权力不能按出价高低分配,就如学校不能按货币支付能力录取学生一样),人们之间的竞争并没有消失,只是从市场竞争转为份额、职位和权力的竞争。竞争的规则也更加复杂和更难完全公平。如果掌权掌勺的人有私心或者制度安排有偏差(这永远很难避免),负面影响有时反而更大。以中国今天的情况为例,我们用基尼系数衡量的贫富差距大的首要原因,是市民与农民收入水平相差几倍的影响,因为这都涉及到很多亿人,所以权重上就特别大,成为中国基尼系数高的主因。市民与农民包括农民工的之间落差,首先又是因为户籍制度,这与私有经济并无关系。其次因为土地制度,市地农地价值差别巨大,分配又极为不公平,造就了无数大大小小的富豪,而我们的土地倒是全部单一公有制的。我们体制内外的医疗和福利保障、退休级别待遇制度长期以来也是差别巨大,体制内的腐败更一度很惊人。18大以来党内腐败受到严重打击和抑制,合法不合理的高待遇也克服重重阻力有所触动和改革,但应当说仍仅仅是起步,要持之以恒还任重道远。
显然,以上所有这些都对我国的基尼系数与贫富差距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实际上都与私有经济没有直接关系,反而与我们的公有制和延续下来的国家管理体制安排有关。所以难怪邓小平当年说,什么是社会主义,我们还并没有搞得很清楚。
现在有些成天喊着社会主义的人,其实并不明白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不明白国有企业并不就是社会主义,共同富裕不是也不可能是同等富裕;
不明白社会主义追求的自由人联合体与国家权力的替代关系;
不明白邓小平所说的实事求是和陈云所说的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才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包括改革开放的精髓。
所以,怎样让社会主义能够实现更大的财富创造、更高的权利平等和更小的贫富差距,还是一个需要从传统概念和本本中解放出来,才能真正回答和解决的问题。
二、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营商环境
这段时间以来,在中央空前明确的肯定了民营企业的地位和作用之后,各部门和各地方都出台了各种扶持民营企业的政策,力度之大,措施之密集,使人目不暇接。民营企业一改之前往往让人避之三舍的窘境,似乎一时成了香饽饽。不讲价钱地保护民企和民营企业家成了政治正确。有的地方甚至下令对民营企业的账户,不能诉讼保全。以至有人感叹:我也是民企,别的民企欠我的债不能诉讼保全,如何保护我这个民企的利益?显然,过犹不及。这种一风吹的摇摆,难以持久,。在历史上,对激进高杠杆企业的救援往往还会助长道德风险,增加经济全局的风险性。这些其实并不是真正稳定和理想的营商环境。
那么,什么是好的营商环境呢?这首先是对产权的真正尊重和法律保护。市场经济表面上交易的是商品和服务,实际上交换的是各自的财产权利。我放弃了自己的货币产权,换来你放弃了拥有自己货物或服务的权利。这里的关键是双方地位平等,不能强取,不能豪夺。所以马克思在《资本论》开篇便说,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麻烦的是,平等和产权这个东西在中国传统中从来最缺乏。中国自西汉起就有“盐铁官营”,赚钱的事朝廷自家就直接垄断了。从春秋末期孔子感叹的“苛政猛于虎”到大唐白居易的《卖炭翁》都可知,就是老百姓维持生计的家当,遇到官府,也绝无平等和产权保护可言。即便各朝各代的巨商大贾,若不识时务,或不知进退,常有性命之虞。中国古代的工商业者,想自立于朝廷做生意,不行。像胡雪岩那样当红顶商人也没有好下场。产权得不到保护,无产者无恒心,这是中国社会财富和资本的积累总被打断,经济发展在历史上长期停滞、在近代严重落伍的根本原因。
改革开放开启了一个新时代,我们也迎来了过去不敢想象的国民财富和国家实力空前强盛的中国。因此,今天其实并不需要对民营企业的特殊扶持和倾斜,而是需要一个竞争中性、不贴政治和所有制标签的营商环境。实际上凡需要扶持和倾斜的对象就已经说明了其弱势地位,本身就是问题。况且,与其他任何群体一样,民营企业本身也参差不齐。不偏不倚,依法办事、惩恶扬善,才是竞争中性。须知财产权本身就是一个法律概念。
故而其二,讲营商环境无法离开法治。法治在这里是指依照明确可依、一视同仁的规则管理市场。规则要改变也要有一定的程序,使人们能够建立合理预期。法治是尊重和保护产权的必然延伸。否则,政府自己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那就没有公平可言。或者政府自己倒是不直接下场,但随意横征暴敛,政策出尔反尔,产权保护也会成了空话。
现在,中国的法治在经济领域的主要问题有三个。一是高标准立法,普遍性违法,选择性执法。我们很多法规要求很高。由于标准太高,不切实际,这样大家都只能想办法变通,规避绕道,乃至阳奉阴违,弄虚作假。由于大家都打折扣没真做,你要老老实实,那基本就要在竞争中出局。地方政府也知道这个情况,故而一些地方也大出土政策,变通执行,进而造成不公平竞争。同时由于法规上明文写在那儿,办事难免要走关系融通。如果突然上面来阵风要严格执行,各级就跟着一齐变脸,老账新账一起从头算。有时甚至刚摆出要严格执行的架式,大家就被吓得魂飞魄散。这次社保基金改由税务部门依法征收,引起全面恐慌就是其中一例。我这些年来年年呼吁不仅要大幅降低增值税、所得税,特别是要大幅降低各项社保缴费,取消强制性的住房公积金。去年我还在中国经济学家2017年年会上强调,我们要从高税费率、低实际缴纳额,普遍违法变通,改为低税费率、宽税费基,严格依法缴纳。这样,由于把更多的人纳入了真实缴纳范围,扩大了社保覆盖的领域和人群,最后收到的税费也未必减少,还有利于公平竞争和增进法治。许多时候,少才是多。财政学上所谓的拉弗尔曲线,讲的就是这么一个道理。
二是所谓窗口指导。近年来政府精简和废止了不少繁文缛节,提高了办事效率,降低了交易费用,减轻了市场主体的麻烦和负担,这受到了普遍欢迎。但政府为了救火或为了提高自己办事效率亦或执行力度,又出台了许多不成文的窗口指导即行政干预,让人们无所适从,非常苦恼,但面对强势管理者,又敢怒而不敢言。现在一些部门说,他们准备要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但人们不知道过去他们的这些干预都是依据什么、从哪里来的,也不知道他们说的不必要的行政干预是哪些,必要的又准备保留哪些,以后还会随时有什么新名堂。不合时宜的法规当然不好,但毕竟还算知道要去拜哪些佛,烧什么香。而这些来无踪去无影的行政干预则更厉害更无章法,让人更无所适从。
三是人大这样相对超脱的正规立法机构因缺乏资源因而自己不立法,大部分立法工作委托政府部门去做。立出来的法当然都是方便政府部门的,而不是从市场主体和社会公众角度考虑,实行起来政府机关怎么做都是他们的理,想整谁一整一个准。这样的机构,人坐在办公室里都有人上供,挡都挡不住。一些原本与经济部门无直接关系的清水衙门,当然也不甘寂寞,抓住机会就挤进审批、发证、备案的队伍,随即也过得风光起来。制度扭曲造成过去公务员们正式收入很低,但家里名酒名烟名牌从不断档,隐性收入更无法统计。这些都成为腐败滋生不息的土壤。
营商环境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条是权力制约。不受约束的权力会被滥用,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不信任任何国家机器的原因。因此,法治的最后一道安全门是权力制约。没有权力制约的法规颁布再多,也不会是法治,而是人治。因为权力没有约束,今天可以这么说,明天又可以那么说,一切随自己需要,自己意愿,自己高兴,结果还是人治。习近平总书记说过:“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权力有没有笼子就是法治与否的试金石。因为法是可以改的,条文也要人去解读。法治是当你认为办事、政策或执法不公的时候,还有说理的地方,还有不怕被打击报复、不怕被穿小鞋,能指望有人主持正义的地方。如果谁有权谁说了算,朝令夕改,你也没有什么办法,利益受损了也不敢吭声。有笼子也是关别人的,钥匙拿在自己手上。这当然就没有法治,也不会有稳定的营商环境。
因此,如果我们想有一个稳定的营商环境,就不能没有对权力的制约。而且其意义,也绝不仅仅在一个营商环境。因为营商环境不可能孤立存在,它是整个经济环境、司法环境、社会环境和政治环境的产物。社会主义在理论上是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没有特权,人人平等和受尊重的理想社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将这一理想变为现实,责任无比重大,使命无比光荣。我们今天还没法像马克思设想的那样用人民的自我武装和直接民主自治管理取代国家机器,因而设计和发展完善对国家权力的制约机制、制约制度,保证权力从上到下无一例外地装进制度的笼子里,就更为关键和重要。实际上,即便是在古代中国,中下层官府及各级官员也不能为所欲为,其权力也还是多少受到制约的。所谓没有权力制约主要是指对顶层权力没有制约。近代以来在权力的使用和制约方面,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最终解体以及我们自己过去的经历中,都有过惨痛的教训。社会主义国家诞生百年以来极为曲折起伏的道路充分说明,能否建立起对国家权力特别是最高权力的有效制约制度,是关系到社会主义国家生死存亡的核心问题,是国家治理现代化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也是在共产党取得政权后,国家机器仍然需要长期存在的新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新发展的必然内容和要求。
三、企业主与企业家
现在,企业家已经成了耳熟能详的名称。我们今天的会也叫中国企业家高峰论坛。但究竟什么是企业家,很多人恐怕并说不清楚,自己认为清楚的人其定义也各不相同。
企业家这个词是从资本主义发育早期的企业主企业那里来的。因为在那个时代,你必须有资本、敢于并能够承担财务风险才能办企业。所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的资本家或人格化的资本,就是企业主。故英语从法文中借来的entrepreneur, 原意即为创业企业家,与冒险创新精神相连。不过,企业即便创立之后仍然处于激烈竞争的市场环境中,企业在创始人之后是归于毁灭还是有更大辉煌,完全取决于继承人的素质。从这个意义上说,企业永远处于再创业的过程中,失败的威胁始终环绕。这样,企业家的概念早就不限于创始人或创业者。
我们今天说到企业家,大家首先想到而且没有争议的就是企业主们,即拥有并掌控企业决策的人。不同的只在于这些企业家有大小与成功与否之分。职业经理人呢,一般就不被认为是企业家了。但这样定义实际上就带来一个很大的问题,即世界上多数大企业、跨国公司的董事长或CEO都不能称为企业家了。因为他们通常都不是企业拥有者,即便有股份也比例很小。比尔·盖茨、乔布斯在微软、苹果很小的时是大股东,企业做大上市后他们的持股比例都很小,用上述定义,他们后来为人所知时就已不能算企业家了。至于当时号称全球第一CEO的威尔奇是作为职业经理人被选任,后又作为职业经理人退休,就更不能叫企业家了。中国很多著名新经济企业由于创始人不占大股,按此也不能称为名符其实的企业家。但这样一来,企业家就主要是中小企业的企业主了,而且特别普遍存在于发展中国家。
越是发达国家的大企业、名企业越没有企业家,这显示我们上述的企业家定义出了问题。其实,这里的偏差源于企业家的传统定义来源于马克思时代的古典资本主义企业。古典企业所有权经营权合一,企业家天然就是企业主,所以这个定义当然没有问题。但随着所有权的多元化分散化,所有权与企业控制权经营权分离,这样企业就进化为现代企业。马克思早就预见到这种分离趋势会使资本家不再是工业企业的指挥官而会沦为投资者乃至靠剪息票过日子、与企业的生产经营无关的人。历史的演变也正是如此,随着两权分离的发展,在很多现代大企业中,原先的企业主消失了,股东变成了千千万万的投资人以及他们的专业机构代理人。因此,在现代企业中,企业实际的经营决策者就是企业家,而且是掌控着比历史上的企业主不知大多少倍资产的大企业家。只不过在现代发达市场经济中,由于股权高度分散、两权分离比较彻底,因而经营者只要未被发现违法违规、侵害股东利益,就有真实的掌控权,就被认为是企业的老板即决策人。就如今天提到世界上迄今市值一度超过万亿美元的苹果公司,大家唯一所能想到的老板就是现任CEO职业经理人库克。依此来看,现代企业家的定义应当指企业真正有决策权的经营者,而与其持有多少股份无关。而我们知道,在中国这样发展中国家中,即便企业披上了股份制和上市公众公司的外壳,但大股东往往还是企业的实际控制人和决策者。公司名义上的董事长、总经理不需任何理由随时可以更换。
这种情况当然与上面说的营商环境有关。在发展中国家,法治环境不健全,委托代理成本较高,发生任何问题和纠纷也往往是大案讲政治,中案讲关系,小案讲法律。在这种环境中,自己用产权和血缘关系控制企业就显得更为可靠。同时,由于宏观经济政策波动也大,往往投机投对了比老老实实做企业会带来更大的收益和回报。显然投机并不需代理人经营企业的才华,而更需要委托人敢于用自己的财产乃至身家性命去下赌注。这种情况不仅造成了投机型企业家盛行,常常风头盖过创造财富的创新型企业家,也造成古典企业和传统企业主模式盛行。
在现代企业中,也会不时爆出丑闻,也有企业家见利忘义忘法,铤而走险。但由于现代企业中的企业家是要靠能力上位、又要靠能力、靠业绩保位续位,因而人选来源和替代选择空间都大,更会有压力始终兢兢业业。同时由于自己尽管也有利益或股份在里面,但总起来是受股东们之托办事,因此通常也不愿以个人承担全部后果责任的方式去违法违规。因而现代企业各方面包括财务的透明度较高,逃避国家法规和应承担社会责任的动力和空间较小,通常员工的待遇、感受和保护也较好。相比之下,很多企业主的企业难免裙带关系众多,家族的人与外人有无形的隔离和天花板。接班人的选择往往限于血缘关系,选择余地很小。这样在第一代创业企业主离开后,越大的企业传承成功的概率就越低一些。特别是企业主企业严重依赖个人能力、魅力、品行。许多企业主在外埋怨政府霸道、官员专横,关起门来在企业内,也完全是一副专制朝廷的做派,狂妄霸道与阿谀吹嘘,让人似曾相识。这类企业主或因经营决策独断专行、头脑发热,或因赌性太重、爱剑出偏锋,难免终会失手,或因个人劣习不改恶性膨胀造成公众或违法事件,这样也会使企业一朝脱轨乃至翻船。
当然,由于现代企业的所有权与决策权分离,因此对其怀疑和争论从几百年前有限责任公司一出现就没有停止过。现代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就预言说,有限责任公司的董事不可能比无限责任的股东对企业更尽心尽力,因此如果前者能胜出,就超出我们的所有常识和判断了。由于上面分析的营商环境和历史文化原因,在中国现在也不乏有企业主型企业家,断言决策人不是主人的企业是不可能搞好的。也有经济学家出来论证所有权、决策权、剩余索取权一致的必要性,按照这种理论,所有权决策权分离的现代企业,更不用说公有制企业,自然被一竿子全打翻。
其实,现在的国有企业就企业形态而言,所有权高度集中在国家,搞个现代企业的外壳也都是摆设,真正的决策权和实际控制人在政府而言,它与肯定也要聘用经理人的企业主企业更靠近,都属于古典企业一族,而与现代企业制度有很大区别。虽然我们提出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已有相当年头,但由于总是离开股权分散、所有权决策权分离这个核心,还在枝节和形式上绕圈子,因而政企不分的问题从来没有真正解决,这是国资国企改革难以突破的根本原因。
微软公司在创始人比尔·盖茨离开,苹果公司在创始人乔布斯去世后, 两家公司分别由我们称为职业经理人的企业家掌控,现在已是世界上排名交替第一、市值近万亿美元的公司。这两家公司的主要股东都是机构投资者,即其实是汇集了千千万万人的养老基金、保险资金、投资基金。这说明现代企业制度在委托人高度分散分层分级、代理环节众多的情况下,仍然可以采用有效的激励机制,发挥其规模、专业化和不拘一格选用人才的优势,在市场竞争中以效率高胜出。从社会角度看,这样的现代企业又不是如企业主企业那样,做成功后是将这万亿美元财富集中在个人和家族手里,而是给了无数普通投资人以自己的小额储蓄参与分享资本增值的成果,改善社会的财富分配和机会平等。所以我历来强调,公有资本和公有经济改革不是没有出路,关键是看我们能否放弃古典企业的控制模式,用股份制、混合所有制的方式实现股权的分散化,对混合所有制企业实行所有权与决策权分离的现代企业制度。实际上,只有现代企业制度的开放性、透明性、分享性才最有助于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追求效率和公平的综合目标。
因此,无论是私有企业要发展壮大,还是国有资本想做大做强,最后都难以避免要走现代企业制度的道路。如果我们的股份制与混合所有制的大型企业,都从古典企业中脱壳而出,成为既非企业主家族企业、也非政府控制、实行行政性管理的传统国有企业模式,那时,非官营而是民间经营的混合所有制现代企业就会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和主流。国有资本和其他公有资本与私人投资一样,自然就会活跃和交融其中。
这样对所谓民营企业的歧视或保护,不用说就都会成为历史遗迹。
反之,如果国有公有资本控股参股的企业,实行的就是与市场化企业完全不同的行政管理体制;
一说到企业家,包括国家表彰的有代表性的企业家,就都只是私有企业的企业主;庞大的国有公有经济没有企业家,只有官员;
现代企业和企业家难觅踪影,那么,公有经济当然就很难搞好,企业家也难免还会是外人。
反之,如果中国混合所有制大型企业的领导人既不是古典企业主老板,也不是体制内一纸任命、拿限定薪酬到点退休的官员准官员,而是以能力上位、靠业绩证明的现代企业家人才,企业管理实行通行的市场化规则,那样,中国经济的繁荣,中国企业的强大,中国融入全球化经济的平等竞争环境都会指日可待。谢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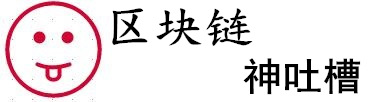 区块链神吐槽
区块链神吐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