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金庸,褒贬不一、毁誉参半的文章我都转了。论才华,他对华人文化艺术的贡献是大师级的。他还是明报的老板,文化商人、企业家,但在行业内的名声并不好。
有人说他的作品是花钱买来的,写手代写的,他包二奶,对待员工苛刻,等等…
其实,这不就是一个真实、完整的人生么。
每个人,都要生存,必须为社会提供价值。
同时,也很自私,满足自己的各种欲望。
金庸虽然小气,但他从不拖欠工资和稿费。而我们,却是在一个封闭、单纯的国度里长大,接受纯洁、理想主义的教育。所以,你们的眼睛里揉不进去砂子。
武侠小说的开创者,不是金庸,是梁羽生。
金庸是浙江人,梁羽生是广西人,梁的年纪比金大。
浙江人,是喜欢浮华、享乐,广西人相对淳朴。金庸有钱,梁羽生贫困,梁在病床上,金庸去看过他,临走时留下一张空白支票。
可是,梁羽生没有在上面填写金额。
为啥?心里看不起他呗。
一个真实的社会,是残酷、现实的。而那些剩男、剩女看着浪漫主义的韩剧长大,对未来充满了期待。他们、她们用挑剔、完美的眼光去筛选世界、伴侣,最后往往一无所有,这是一种爱无能。
理性的人,成功之处就是跟世界妥协。所以,心大的傻逼才是人生最快乐的赢家。
世界和人性,既干净、也脏。放掉那些不切实际的幻想,你也可以快乐起来。
哦,对了,最后例行塔哥品牌口号:北京、上海、深圳的房价都会拦腰砍断!
人无完人,活出自我才够精彩,别太在意他人目光,活成了人设。心怀理想,与现实友善和解。
金庸的第二次婚姻,是和才女朱玫缔结的,在长达20多年的婚姻里,两人可谓共同度过了人生最好的时光,而这段时光,也是他们事业由最艰难走向最辉煌的时光。
结婚初期,朱玫身为英伦大学新闻系毕业的记者,一手协助金庸办明报,一手抚育刚刚出生的幼孩,她前后生育了四个子女,同时还不间隙地为明报撰写大量的新闻稿件和时评,最困难的时候,她左手抱着孩子,右手还在赶稿写字。
然而,近三十年的携手共度,抵不过一个男人临老入花从的色心大动,也抵不过一个饭店女侍的青春机黠。
五十多的金庸时常在明报附近的一家咖啡厅用餐,一日,他留下十元小费后离开了咖啡厅,而后面一个年轻的女侍却追上来找他,将十元钱还给他,很“真诚”地说:“文人赚钱不容易,所以不能收这么多小费。”金庸大为感叹一个贫贱的女侍如此不贪财,于是公布自己身份,留下了自己的联络方式,两人从此热络起来。
——稍微有脑子的人想一想也知道,金庸其时已经名满香港,明报更是大报,他常去的附近的咖啡厅,老板和女侍会不知道他是金庸?需要追上来还他这十元小费?
然而,到底是金庸先放下这笔小费钓鱼上钩,还是女侍善捕捉春风,只有他们两个当事人才知晓了。
16岁的女侍很快成了金庸的情人,两人在跑马地附近租巢同居。
而依然在明报工作的朱玫,是最后一个知道丈夫奸情的人。
其时,他们的长子,已经18周岁,正在美国读书。
金庸提出了离婚。他似乎已经想清楚了如何享受他的余生。而他的长子,因为恳求父亲不要离婚未果,最终选择了从21楼跳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即便如此,金庸依然执意离婚。
对于他来说,他已经有了足够的金钱和社会地位,永保自己在未来的老年,搂着一个青春丰泽的肉体享受余年。
他甚至对所有的朋友说,他要求离婚的原因是因为和前妻朱玫没有共同语言了。是啊,他和一个同等学历,同样职业的老妻没有共同语言了,而和一个连国中都没有读完的女侍倒有共同语言了。
真奇怪朱玫当年青春明艳、才气过人,帮他自贫寒中超拔,两人携手创业的时候,那么漫长的没有共同语言的近三十年岁月是怎么度过的。
朱玫最终签字放手。
她的人生已经毫无希望,坚强如她,终究没有从这一次打击中恢复过来。长子早逝,丈夫背叛,娶一个十来岁的新妇入门,年过五十的她,人生如何重建?
她已经没有足够的时间去治疗人生创伤。
她独自冷清地过了一段时间,对人,始终不道一声“苦”。
几年后,61岁的朱玫因癌症在香港去世,死的时候,连死亡通知书医院都不知道该送往何方。
想来她是伤透了心的吧?对人世,对自己,都这么决绝。
而此刻,金庸大侠正拥着他娇滴粉嫩的小娇妻,环游世界。那16岁的女侍自此超拔,从一个前途无着的街头贫女,一晃成了上流人士的夫人。连亦舒、林燕妮等见了她,也不得不敷衍一二。
金庸更拿出大笔金钱,送她去澳洲留学,好歹镀了一层金。此后,永远随身携带他这个美人,周游列国。古代文人素有老来娶美妾,然后携妾游山玩水的雅兴,每每游玩之后,写上一篇文字,落款为:某某,某年某月,携X姬于某地。
他们是这样公然地炫耀和享受着人间一切资源。他们是这世界的中心,一切的美好事物,并非与他们平等共存,而是仅仅供给他个人的享受使用。他们在捍卫自己权利时何等不留余地,而在牺牲别人时,又何等毫不犹豫,此后,在写起道德文章时,又何等气壮山河。
人世间背信弃义者多矣,人世间无耻之徒多矣,但象金庸这种文章里大义凛然,情意缠绵,真爱悱恻,而事实上道德操守却猪狗不如的文人,我再没有见过第二个。
其实我很好奇,如今年过八十的老金庸,搂着他青春年少、情欲旺盛的小妻子时,他妻子的人生,到底美满与否?幸福与否?
对于这些完全不符合自然规律的结合,我并无歧视,我歧视的是,他是践踏了另两个灵魂和生命,来成全了自己的肉欲(假如他还有肉欲的话)和幸福的。
这样流着鲜血的婚姻,也能理直气壮、扬扬得意地在阳光下受到祝福么?
又,金庸曾追求香港影星夏梦。而夏梦认为他并非良配,最终嫁给了一富家公子,移民美国,迄今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而金庸为了泄恨,在《鹿鼎记》中以夏梦为原形,写了阿珂,同时将夏梦的丈夫写成了英俊倜傥多金的郑克王爽,在文章中将这二人折磨再三,意淫再三,郑的下场极惨,而阿珂也下场极惨,必须要他(韦小宝)前去搭救。
又,金庸对报社编辑记者极其苛刻,从来不思厚待,以亦舒林燕妮和他的交情,以及为报社作出的贡献,他所给薪酬从来都是苛刻到极点,亦舒屡次提出抗议,他都说:“给你加钱有什么用?反正你赚钱也不花。”而对林燕妮,他的回答更妙:“给你加钱也没用,反正你都花掉。”而他自己,对待那个16岁的女侍,则一掷千金,纵容挥霍。
总而言之,在他而言,苍生他人,皆是刍狗,道义信条,都是空文,而他的欲望,他自己欲望的满足,才是唯一的中心。
中国男性文人之恶劣自私集大成,金庸之一生,卓然典范者也。
从「四大金庸小说」探索两个查良镛 │吴霭仪
从小爱看金庸的武侠小说,一直到年长,不知看过凡几十遍甚至百遍,金庸笔下创造的那个奇幻而又文化色彩浓厚的世界,为我这一代人提供了丰富无比的精神食粮。但我并不崇拜金庸。事实上,谈论金庸小说,最令人烦厌的,就是那些排山倒海的吹捧文章,而这些文章,不幸又影响金庸对自己作品的看法和不住的修饰和演绎,以致破坏了原著的真面目。我始终认为,有瑕疵的真,远胜于完美的假。
文学的金庸
金庸的武侠小说,是每天在报上连载写成的,初时在《新晚报》、《香港商报》,创办《明报》之后,就在《明报》连载,主要目标当然是为吸引广大读者,内容与风格,也自然需生动有趣而且能製造悬疑,吸引读者一天一天的追看。这个方式无疑有其限制,但无损真正有天才的作品的质素,许多世界名著都是这样写成的。到了结集成书,有机会从头至尾翻阅,总会修改一番,尽量减少前后矛盾等毛病,令读者看得畅顺一点,但要将原著改头换面,大肆修改,效果却未必理想。
一般来说,我认为金庸小说旧版胜于新版,最显著的例子是改动得最大的《射雕英雄传》。金庸以加强结构及删减枝节为理由,删掉了南琴的故事,将这个人物与穆念慈合併为一,连带删去了血鸟、蛙蛇大战等离奇场面。我不赞同,不单是因为南琴这个人物和故事写得极好,删掉了太可惜,而是从文学角度,南琴的遭遇与黄蓉的对比,加深了小说的层次。将南琴被杨康姦污成孕的故事,移接到穆念慈身上,破坏了穆念慈这个人物的个性完整,破坏了穆念慈与杨康恋情的凄迷,还换掉了杨过的亲生妈妈!
修改为了更高雅?
《射雕》的修改,还有很多我认为是画蛇添足的地方,例如将黄蓉烧给洪七公吃的菜变得更风雅、添了曲灵风隐居牛家村的楔子等等。但我最大的反感是,金庸要将自己的小说,不只《射雕》,改写和包装得更高深博雅,刻意删除可能被视为庸俗无聊的部分,将整套金庸小说全集变得更高格调,是为了配合那些吹捧文章力求把金庸小说提升至殿堂文学的地位,令其更符合金庸建立了的文化及社会地位。原本的金庸小说,已能令金庸的地位在创作文学上并世无双,何必刻意改变自己去追求某些权威的认许?
我无意低估查先生的社会文化地位,事实上他创办《明报周刊》,特别是在文革时期创办《明报月刊》,敢言无惧,得到了香港知识分子的尊重推许与认同,是毋庸置疑的,我只是不认为金庸需要改变自己的原著去配合他的与日俱升的社会地位。举世称雄的大文豪莎士比亚从来不需要删掉他的戏剧里的粗言秽语和低俗笑话。高级知识的口味不限于高深博雅的作品。众所周知,大哲学家罗素,是雅嘉莎.基利丝汀侦探小说的忠实读者,谁也不相信这些精采绝伦的侦探小说要争取文学地位。我认为,一部作品的文学价值在于它的真;雅与俗,任何格式,感动我们的也是真诚,愈是为观念、品味正确而修改,就愈会削减原著的真,改得多完美也不能弥补。
政治的金庸
1986年,我在《明报》办事,每天在副刊发表论金庸小说的专栏,后来结集成书,旨在娱乐读者,也在提出自己对金庸小说的不同体会和批评,写到后来,渐渐变得认真甚至沉重,那是受了当时香港局势的影响。1981年至84年,中英谈判期间,《明报》发表了多篇由查良镛亲自执笔,很有分量的社评。中英联合声明签署之后,中共正式展开了草拟基本法的工程,而查先生是受委任为起草委员会的港方委员之一,他的参与直接影响到香港九七后的前途以及过渡时期的香港状况,他的个人观点和决断,就成了左右大局的因素,从政治角度分析金庸小说表露的思想,也就变得难以避免了。
从政治角度分析金庸小说,其实十分自然。例如《笑傲江湖》就普遍被认为是隐喻文革的政治小说,其中东方不败是影射毛泽东。但从广义的政治,我看的是一个对国家民族有所承担的人,在乱世之中如何面对自己的个人理想与责任。金庸从1955年开始写武侠小说,直至1970年左右共十五年,然后从头修订,又费了十年工夫,至1980年完工。这个年代,中国内地经历了重大的变化,旅港的文人大多对政治襟若寒蝉,但他们对中国文化及中华民族的前途,有很深的忧患意识,这种意识,强烈地流露在他们的作品之中。
我在结束整个金庸评论系列的部分,介绍了我挑选的「四大金庸小说」:《射雕英雄传》、《天龙八部》、《笑傲江湖》和《鹿鼎记》,从这四大小说,可以看到金庸的政治观的发展。我认为这个发展,是从单纯到複杂,同时也是从乐观走向悲观。
《射雕英雄传》是以汉人的宋朝为中心,是个外族入侵、朝廷积弱的局面,英雄侠士的责任就是拼死保卫国土百姓,虽然最后牺牲也是值得的。
在《天龙八部》,汉族王朝已不再是中心,天下四分五裂,多民族的局面,忠奸正邪已变得随身份观点而异,盖世英雄如乔峰,也逃避不过这个命运,最后天地之大,无容身处。世间灾难无了期,只能在佛法的慈悲里寻求个人的解脱。
《笑傲江湖》没有朝代历史背景,主题是政治斗争,再没有救世的英雄;武林泰斗,不是野心家就是伪君子,真正的性情中人,最后只有抛弃社会一途。但同时值得指出的是,《笑傲江湖》的主角令狐冲,也是金庸小说中最高贵的道德典范,他的道德情操,表现于他在正邪善恶、真诚与虚假之间良知的抉择。
我的结论是,比起《鹿鼎记》,《笑傲江湖》的政治观还要显得单纯而天真,因为政治这个肮葬的问题,不会因个人退隐而消失。只要有人统治,这人就要面对複杂的政治问题,他不能靠武功、理想、个人品德去解决问题。
英雄可以杀身成仁,但统治者却要尽力维持长治久安。
我说:「表面上,《鹿鼎记》表扬了康熙的成功有为,但这部小说的悲观,是道出世上原无乾淨的成功,理想必须屈服于现实之下,要得到积极的成就,就必须懂得妥协。到此,金庸从政,也差不多是时候了。」
金庸的死结
查良镛政治的死结,在于他无法接受民主。他推许人权、自由、法治,主张中国收回主权、成立特区、港人治港,但他深信不能在香港实施民主政治。他在1984年1月9 日《明报》的社评说: 因为实施民主政治,会令香港的稳定与繁荣及现存的生活方式难以保存。他所提倡的政治制度,是以协商方式,产生各行各业的议会代表,然后再由议会代表协商,推举「市长」。
我要讨论的不是究竟这个政制行不行得通,而是在这样的构想之下,有分量的文化人如金庸所扮演的角色。这个角色,不是英雄侠士的角色,而是幕僚、说客、甚至「国师」的角色,向当权者提意见,力求这些意见得到接纳、实施,从而对施政有良好的效果。
然而,这个角色的先决条件是要找到一位英明的领导人,然后争取这位领导人的信任和重用。世上没有道德完美的统治者,《鹿鼎记》把康熙写得那麽英明伟大,也不隐瞒他必须用奸诈而残忍的手段,而要争取他的信任,可能就难免要做韦小宝那样的人。跟皇帝做朋友不是那麽容易的,未当权之际可以做朋友,但要懂得分寸,说话要中听,知道最终也是主子跟奴才的关系,而到了最后,即使机智世故如韦小宝也吃不消,只能认输:「老子不干了!」
查良镛的角色远远不是韦小宝,他得的尊敬,和地位的尊崇,是有目共睹的,然而,韦小宝这个角色,勾划出极权下领导人的诤友最终可能所处的位置,而在过程中,远远在抵达最终位置之前,变化已在不知不觉中开始发生。我们可以看到,金庸在修订新版《鹿鼎记》的过程中,甚至在其后的评论解读,把韦小宝写得愈来愈容易接受,甚至可爱,在文学上在政治观上都令人遗憾。
在政治观上,美化韦小宝的角色是不道德的,写实就是写实,即使出于政治需要有时要作出违反原则的事情,也不必将它说成无伤大雅,甚至值得欣赏。
从文学上,我更加认为美化韦小宝是败笔。虽然基于主观理由我最不喜欢《鹿鼎记》,但我认为这是金庸最成熟,写得最好的作品。这是金庸突破自己之作,初出版的时候引起了「金庸迷」极大的争议,正因为韦小宝一反金庸主角的常态,是个低俗粗鄙的小人。但金庸侠士已写到尽头,《鹿鼎记》是一部讽世小说,所以主人公恰如其分,也是个市井之徒。《鹿鼎记》写得好,因为它热闹、有趣、从反讽的角度看传统的仁人侠士的世界。它的成功,在于它的疏离、玩世和嬉笑怒骂,视禁地如无物。但一旦对某些人物变得认真甚至认同,小说便不再疏离了,变成宣扬新的道德标准,为之辩护,失去了原来的意义。
结论
金庸在香港文学政治与文化历史上的重要地位,无人能质疑。无可否认,他的某些政治立场与做法备受争议,但他的小说为一整代人带来了无可比拟的启发和享受,塑造了一整代人的思想与民族文化认同,金庸,或查良镛在政治或其他方面的缺陷,也不能抹杀这些重要而独特的贡献,为此我们应衷心感谢。
刊《明报周刊》,2018.10.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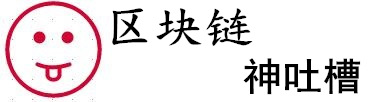 区块链神吐槽
区块链神吐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