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弈对冲交易者@wangwatchworld
在十二年之后,我特地选择了同一个地点。
十二年前,我们三位做大宗商品的同行,从早晨10点到凌晨1点畅谈了对未来所有的预判。
并看到了我们的预判。
这一次少了一位,他去忙于数以亿计的官司去了。
幸免于大时代风暴的两位老友,在南半球别后九年再次相聚,这一次我们畅谈了二天。
这一次,我们不再预测未来,只谈认知。
不过在九年间未见,老友调侃我和其他的一些言论大v,试图做国师或有家国情怀的思维。
我坦然说,他知道我没有国师的理想,曾经有家国情怀的顽固思维,在过去的九年中已经荡然无存了。
一切都已经磨损。
但这不是真实的我。
我说或许我没有假装还有家国情怀,但很多人还误以为我有。
其实我想遨游于四海之间。
记住区别,我并没有庄子游的思想,遨游于四海之外。
我遨游于四海之间。
上一次我跟一位体制内的朋友谈及我为何不触及政治话题,坦言道:
人类这种微毛的生物,存在与否,对造物主的宇宙与智慧,没有任何的影响。人类终将毁灭,而毁灭之后,宇宙仍旧在那里。人们发现的一切知识,都不过是万物存在的哲学,宇宙信息洪流中的一点点星光而已。
人类既然所有的行为都将走向注定的结果,我作为微茫的人类生命中的一根鸿毛,说与不说什么,都是不重要的。
我没觉得我有什么重要,我也没觉得我会改变什么,无论我做什么与不做什么。
人类的贪婪和愚蠢,谦卑与智慧,都不过是时间与空间的影像而已。
在这一世中,你我拥有的财富与贫穷,欢愉与悲伤,都是不重要的。
上帝不在乎。
我们在海边栈道漫步时,谈及某个知名的人物在牢狱里,我对朋友说:我们俩和他没有区别,只是牢狱的大小而已。
朋友脱口而出说:对。
而我们的思想遨游于四海之间,宇宙之上,也可以说他的天地与我们是一样无限。
朋友提及我以前提及的一个经济学理念,这个理念单纯的放在经济学里是无效的实验室理论,放之四海则反应人类的愚蠢和狭隘。
在宏观经济学领域里,自由市场是否可以完美的达到帕累托最优?
资本可以遨游于全世界,但劳工无法自由迁徙。
实际上马克思同学陷入了思维的误区,后世宏观经济学也无法诠释人类制度对资本与劳力的关系。
如果世界没有城墙,没有国家的边界,资本与劳力都可以自由迁徙在全世界的任何地方,劳力和资本自然而然的博弈均衡,则全世界不存在国与国之间的贫富差距。
也就是当美东的工人有7万美元一年的工资时,非洲的工人只拿着700美元一年的工资。
在没有国界的世界里,全世界的劳工会流向美国,直至全球的工资趋于一致。
资本丧失了全球工资套利的空间,也就留在最适合商品与服务流动的地域,形成一个个巨大无比的世界级港口大都会,进而在这种完全竞争下,走向完全的比较优势和技术创新,制造需求,人类的进化得以提速。
但是这显然不符合人类贪婪与掠夺的本能,玩弄国家的权力阶层势必要垄断资本与劳力的涌动,人矿是每一个矿主想要把握的资源。
这就像极端的专制国家北朝鲜要控制他的国民完全奴隶化,不要流动。
而多数呈现的是各个国家政府竖起海关壁垒,堵截全球的劳力流动迁徙。
他们内部本身的人矿要抵御其他国家的人矿过来,以免削平溢价。而控制这些人矿的权力阶层,得以以选票或其他方式获得权力,并获得税权,向资本和劳力征收财富,并养活整个权贵利益阶层。
这就像某人所说的“财富像木制大屋,权力才是难以摧毁的石制殿堂。”
实质上就是合法的掠夺权。
但是我们回到人类制度经济学本身的一个诠释,就像过去纤夫在河上拉船,纤夫们共同出钱,请了一个监工,用鞭子来抽打他们维持规则,以免滥竽充数的纤夫搭便车。
这是政府曾经出现的意义,政客与事务官签署了协议,以维持国家的规则与秩序,并提供安保。
但政府顺便关闭了国门,以免对他们不满的国民会以脚投票离开,导致税源下降。
国与国之间以外交达成默契,堵塞人类的自由迁徙脚步,是因为所有的契约政府,肆意扩大和窃取了委托人的利益,远远超出了维系一个国家规则的成本。
人类为自己这个物种的不守规则和不自律付出代价。
但人类永远不会像蚂蚁一样,生来就安排好了职责,听从于基因的安排。
这不过是人类自身制造混乱,从自私和贪婪制造的混沌状态行,形成黑箱模型,向前进化。
错误来自于自私和贪婪,并带来突变。
即使如此,人类本身是应该自由迁徙的,这是真正的自由和选票。
一以脚投票可以击碎权力本身的错误,他们在丧失供养后,才会服务周到。
但是玩弄权力的人类权贵本身又是聪明人,因此他们堵截了人类的选择权,付诸于一个虚假的民主,或者干脆置之不理,完全专制。
自由市场和竞争自始至终就是不存在的,当人类的权力体系建立后,资本和劳力就各自寻求垄断利益的模式,前者是托拉斯,后者是工会。
之后又开始比烂,资本影响的国家还能保有对知识技术创新的鼓励,以外部性影响资本和劳力结合的供需平衡;权力控制的国家就完全付诸于掠夺。
在这种比烂之下,国家就更加的封闭国界,欢迎资本的到来,杜绝劳力的移动,即杜绝劳力离开,也杜绝劳力进入。
前者是权力阶层,后者是劳力支持的权力阶层。
很少有能自由来去的人们,哪怕是豪富阶层,因为各国政府还把他们的财富视作统治阶级的财富。
既包括他们的物质财富,也包括他们的智慧与技术。
当然愚蠢的国家,是不会在乎智慧与技术的,只在乎搜刮物质财富。
回到我们漫天闲扯的废话,谈到个人的抉择与生活。
遨游于四海终究是现实中无法实现的,在不同的国家付出不同的门票钱,迁徙生活,也只是看似自由而已。
这段话的消极不是我朋友想要的。
朋友所说的那种遨游于四海是积极的生活方式,唯有臣服于神,在神之下任何人无法约束自己,终究会使得自己成为人类系统追逐的病毒,一个bug。
https://mp.weixin.qq.com/s/ZBl8MEDIXTl8NyzLYvGuPA
逍遥游-下篇
为了更有仪式感,三天后,我又回到了原来的地点,重新定了同一个房间,来写逍遥游的后半部分。
呃,真相是我把所有重要的证件和卡忘在了酒店的保险柜里,不得不回来取,当日又走不掉,就索性住在同一个房间了。
衰老过早了来到了我身上,我的记性很糟糕。
我的一生是沧桑的,有一半是我被动接受命运,另一半是我主动选择。
在我这个年龄的大时代背景下,我在鲁西北的农村出生长大,公粮大部分上交后,就生活在极度贫困和饥肠辘辘中。
而落实政策,当我跟随母亲回到上海父亲的身边后,缺少陪伴和教育子女经验的父亲用高压的教育方式对待了我们。
中年之后,我走出了原生家庭的创伤,似乎每一个同龄人都有过。
我在最近才知道兄长一生没有走出这段创伤,尽管他在美澳已经功成名就,是美国顶尖的科学家。
在精神世界走出父权社会的烙印,用了大半生,幼年的十年是宏大叙事下的威权,青少年时期的十年是微观世界的父权。
我曾愚笨的用厌学来逃避高中的高压,后来用荒废大学的四年来放纵自己压抑的心理,这带来了巨大的代价。
因为尽管我在外资涌入的大潮里享受了早期大学生比例过少的红利,在外资企业打工多年,薪酬不菲,且早早的游历北美两个国家。
但是我在创业之后,立即遭遇了知识匮乏、生活经验不足、商业投资技能近乎为零的报复。
一败涂地,重新陷入困苦中。
破产岁月的身心重创,直至老年时,直接显示除了脆弱的一面。
这也伴随着家庭的损害,妻女的健康均不如意。
我洞悉了黑暗的一面。
当你凝望深渊,深渊也凝望着你。
凝望深渊过久,你就变成深渊。
在33岁左右,我重新学习知识和自由的意义。
在40岁进入大宗商品领域,这是金融业的一部分,继续学习、试错、摔倒和爬起,无数的失败,零星的成功。
这一次是重生的第一重蝉蜕。
然后半途中退出,为了女儿的成长,选择远渡南洋,半退隐八年。
与女儿一起重新成长,经历青少年。
我是个巨婴,时代造就的。
尽管我在二十多岁时枉谈自由,但我并不知道。
我在40岁至46岁时褪去了巨婴的第一层皮,有了自力更生的铠甲;
我在46岁至50岁间褪去了巨婴的第二层皮,重新体验了青少年时代的成长,获得认知家庭的爱与责任。
代价是女儿的成长并不顺畅,因果从上世纪的七八十年代延续到她的青少年,我依旧继承了父辈的不妥,部分的,尽管我极力的抗拒了大部分,我所厌恶的那些,剔除了,只剩下责任和爱,但阴影顽固的烙在自我。
这就像数千年的华夏,烙印在你我的潜意识,人格和自我上。
某些时刻,我恐惧的面对自己和孩子,怕她重复我的前半生性格和自我。
直到大瘟疫前与中,学校里中国孩子的离去,我们相处的时间更加松弛,她的异域同学们展示的友好性情,最终让我看到她的成长,健康的一面掩盖了我这个“原生家庭”带去的创伤。
在我母亲重病去世的时段,我无法陪伴她去北美。
她独自去了北美,孤独的第一晚是在酒店大堂度过,因为我彼时心不在焉,没有计算时差。
她在黑夜里与我视频,一边安慰我,一边不自觉的流泪,说爸爸你不要担心,我只是忍不住要哭。
我焦灼的在线上陪伴她到黎明,因为我听说多伦多那个区域治安不好。
她独自离开,没有住酒店,叫车去了学校,从此展开了成长的另一个阶段:离开父母,独自成熟。
似乎这一刻,催化了她心灵世界的坚强,非常顺畅的融入了北美的生活。
在那个月之后,我心理的锚突然断了,回到了自身的根基。
那晚在港口散步,高楼灯光倒影在海面,波光粼粼。
我跟老友解释一些人的精神世界,需要一个锚,有的人是锚定一个国家,有的人是锚定家庭,有的人是锚定价值观。
我的锚一直变来变去,我的精神世界也变来变去,尽管自十四岁起我读了一本书,深受其影响,认定人是应该自由的。
但我的自我和潜意识都不稳定,锚也飘来飘去,就像某些人说自己信仰什么,但灵并未入住。
古人说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
我四十岁知天命,之后十年陪伴妻女,在偏远的海岛恢复身心健康,五十四岁才目睹亲人的去世整个过程,大恸之后才不惑。
这句话说起来难,做到也难。
你要自由的生活,就要在这个物质世界拥有自由的财富基础,这个财富可以是物质的,也可以是智慧的。
物质财富来源于智慧。
而智慧不仅仅代表知识技能,还代表勇气、坚毅、想象力、追求自由的本心与创造力。
你要自由的迁徙,还要与整个世俗的权力社会去博弈融合,而非跪倒。
而老友所说的积极的自由,是自身置于权力社会之上,自身成一国,与庞大无比的世界统治机器平等而立。
他的精神世界比我更强大。
在神之下,没有仰视,众生与诸国平等。
在所有的权力阶层那里,这都是敌国。
终于我们说到终极的自由,目前只有马斯克在尝试,他或许在某一天到达火星,就此真正的一人成一国,与蓝星平等。
他尝试了做选帝侯,成为帮助大统领成型的人。
那意味着不仅仅是泼天的财富,还有顶破天的创造力与勇气。
所以那天我明白了老友所说的遨游于天地,双膝绝无可能跪在神之外的任何一处殿堂中。
我精神上能做到,智慧不足,就只能做遨游的浪者了。
https://mp.weixin.qq.com/s/MSfCEeJn2oBfGmEzlAWu0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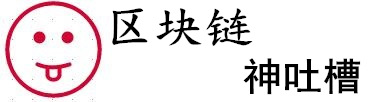 区块链神吐槽
区块链神吐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