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晓阳:记念我的母亲
褚家朝新注:
遵《二号首长》作者黄晓阳先生所托,转其记念刚刚病逝的母亲的文章。愿老人家安息,请黄先生节哀。
一、母亲的归途
2022年12月23日晚7:35分,我那一生坎坷命运多舛的母亲,走完了生命最后一程。
图片
黄晓阳注:照片拍于2020年国庆节,我的儿子、儿媳带着一岁半的小孙女回到黄石。父母和长子(我)、小女儿、孙子、孙媳以及曾孙女四代同框。十余年来,一直是小妹在无微不至地照顾两位老人。
这次生命的归程虽然平静,却早有预示。
早在八年前,我家空了几十年的老屋基,终于盖上了三层小楼,父母兴高采烈,从黄石搬回了老家。那时,母亲虽已八十高龄,却是她生命中最为青春的一段时光,每天,她无数遍打扫房前屋后,似乎有使不完的劲,完全不知疲倦。
对于生命,我们永远后知后觉。
看到母亲如此的精气神,作为子女,我们只是沉浸于兴奋,却疏于防范,乐极生悲,于是乘隙而入。
一天下午,母亲踏上短梯,想从衣柜的最高层取下几件衣物。
衣柜顶层只有我伸手的高度,毕竟母亲较矮,她需要借助木梯,踏上一至二级,也就是增加了二十厘米左右,甚至不如一张凳子高。
事后推测,正因为她觉得自己身体状态很好,又只有那么一点高度,才决定自己做这件事。正是这一点疏忽,意外钻进了我们谁都没有注意到的缝隙。
母亲从梯子上摔了下来。
妹妹和堂弟将母亲送进了大冶市人民医院,检查得知,母亲的半月板碎成了四块。
此前,我一直担心母亲会在某一天向我们告别,却并不完全知道,母亲的生命归途,从这一天正式开始了。
我从长沙赶回大冶,和医生一起商量治疗方案。路途中,我已经咨询过很多人,最终摆在我面前的,还是两个方案,一是动手术,一是保守治疗。所有专家都说,两个方案,各有利弊,对于她这种年龄的老者而言,不存在哪一个方案更好。
最终,我不得不拍板,保守治疗。
哪怕我问过很多人,工作仍然做得不细。我们不知道一个常识性的规律,老年人一旦摔跤,由于治疗以及恢复期,长达几个月的卧床,极容易导致血管栓塞等情形,从而引发中风。现实中,一个相当比例的老人,都是因为摔了一跳,不久引发中风离世的。
半年后的一天,母亲的手突然出现颤抖,肌无力。小妹的公公因中 风离去,知道这是中风的先兆,迅速将母亲送进了医院。
虽然是中风,毕竟送医及时,如果治疗过程中,我们能做得更好,恢复情况会好得多。尽管医生和护士一再提醒我们,要强迫母亲多活动多行走,我们也照做了,却做得远远不够,一旦母亲大喊疼痛,作为子女,不忍看到母亲痛苦,心软了。
就是这种内心的柔软,让我们狠不下心,没有采取逼迫的方法,强制性地令母亲保持足够的活动时间和活动强度,事后总结,若是当时能狠下心,将活动强度和频率扩大一倍以上,假以时日,母亲应该是可以恢复正常行走的,能多活几年的。
可怜天下父母心,其实也可怜天下子女心。有哪个子女,愿意看到上亲承受难以忍受的疼痛?可遇到这种事,任何不忍,都可能带来更为严重的后果。
等我们意识到应该狠下心,强迫再强迫的时候,已经错过了最佳时间,母亲的一边手脚瘫痪了。最麻烦的是,瘫痪的那条腿,竟然是摔伤时未受伤的那条。
后来的七八年时间,母亲只能用那条伤腿,支撑着整个身子,拄着拐杖,顽强而又执着地走动。
这样的风烛残躯,极容易再次摔倒,许多时候,并不因为某种障碍,甚至仅仅因为坐的时间长了,站起时腿不得力。几年间,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在不经意间摔倒,尤其最近一年,竟然摔倒了三次。
最后一次摔倒发生在几天前,正是疫情管控刚刚放开的时候。
事后回想,那天她的状态貌似又是不错。平常,她起床时,总需要小妹帮忙,可这一天,她竟然自己翻身下床。她还对小妹说,今天她感觉很有力,自己就能坐起来,并且把腿放在地板上。
小妹用轮椅将她推到厕所,刚刚转身去照顾父亲,却听到轰的一声响,迅速跑进房间时,发现她已经摔倒在厕所里。
疫情严控刚刚放开,羊群在神州大地四处流窜,如此特殊的时期,小妹一个人根本无法将母亲送医,只能让她静卧在床。
那几天,我几乎天天和小妹通电话,商量请一个人帮助小妹照顾两位老人,这个时候想请人,真是一件大麻烦,每个人都担心出门便遇到羊群,我们也担心新请的人将羊群带进家门。
12月22日,小妹夫经历了几天与羊的搏斗之后,稍稍好转,便赶到了我家。当天,我曾和家里视频,躺在床上的母亲,和我说了几句话。在视频中看到母亲的那一刻,我的心猛地往下一沉。
这个躺在床上的垂暮老人,苍老而又衰弱,生命似乎仅仅只是她的躯身之上,飘游着的一团雾。
但即使如此,我以为她仍然能渐渐恢复,以便我有从容的时间,回去陪伴她一程。
23日中午,突然接到小妹的电话。小妹在电话中说,她和妹夫商量过,决定将母亲送回老家,并且征求过父亲的意见,父亲表示同意。他们担心母亲在世的时间不久了,希望我赶回去。
我心中大急,一时难以决断。毕竟,我可能刚刚与那只羊撞上了,身体还没有恢复,浑身无力,妻子晚了三天,正是浑身不得劲的时候,根本不可能驾车。这个羊群肆虐的时期,哪怕是出门这样的小事,都变得异常严重,我只能一次又一次和小妹通电话,了解情况,希望老母能再坚持几天,以便我们状况再恢复一点。
妹妹和妹夫一直联系救护车。
这个时期太特殊了,他们分别联络黄石和鄂州,得到的回答是,所有救护车都排满了,派不出来。他们只好联系我的大妹夫,身在武汉的大妹夫通过关系,联系到一台商业服务公司的救护车,需要在完成最后一趟送医任务后才能到达,时间应该在一个小时之后。
晚上约7点,救护车到达。他们将母亲抬上车后,小妹又给我打电话,说,救护车上的医生看了母亲的情况,认为很不好,估计熬不过当晚,至迟是明天,要求我立即赶回去。
我不得不考虑另一方案,给一位朋友打电话,希望借用他的司机。司机小陈五天前就阳了,仍然在咳嗽,至于是否转阴,并不清楚。
到了这种紧急的时候,我完全顾不上许多,只问,他能不能开车?朋友说,开车应该没问题。我说,那就请他辛苦一趟,连夜将我们送回去。
就在等待小陈的时候,7点36分,我接到小妹的电话,哭着告之,一分钟前,母亲走了。
24日凌晨两点,我赶回了老家。
小妹哭着对母亲说,妈,我哥我嫂赶回送您了。
我摸着母亲的脸,已经没有了温度,再摸母亲的腹部,还是温热的。
母亲走完了她生命中的第89个年头,就这样和我告别了。
二、母亲苦难的童年
母亲姓方讳秀英,出生在湖北省鄂州市(当时的鄂城县)洋泽乡草鞋方,时间是1934年阴历二月二十六日。
我在网上查询,当年的洋泽乡似乎改为现在的泽林镇,草鞋方大概也是过去的旧名,不知是不是现在的杨方村。这一年是甲戌年,属狗。这一天,是阳历4月9日。
母亲出生的这一天是祥瑞还是平淡,已经无法查证。我从父母口得获得的有限信息,给我留下的强烈印象是,随母亲而来的,是接踵而至的苦难。
有关她的家庭,她自己的记忆并不多,大多是通过大姐以及亲友们的转述,很简略。母亲是家中的第三个孩子,也是第三个女孩。
母亲的生父,也就是我的外公,讳名方太阶,由于其父是一位乡村郎中,酷爱读书,虽家徒四壁,却是当地藏书最多的人,我的外公也因此受了熏染,成为当地最有文化的人,年纪轻轻,便开始在私塾传授课业。
外公思想新潮,是当地反封建的先锋人物,崇尚新文化,在当地积极提倡妇女放脚,男子剪发。故此,母亲的一双脚,仅仅只缠了很短时间,稍有畸变,仍不失天然。
后来,革命军兴,外公投笔从戎,参加了国民革命军,随后被派往湖北恩施服役,抗战时曾给家里写过一封信,从此再无音讯。文%¥革后母亲曾试图寻找生父,多方打听,却杳无音迹。
母亲的生母,也就是我的外婆,不知名,只知姓杜,乡人称为杜氏。或许因为生育,或许因为家穷,外婆的身体状况一直不佳,以至于没有奶水喂养母亲,在母亲两岁时,便一病不起,撒手人寰。此时,母亲姐妹三人,便由当乡村郎中的祖父养育。
我这位外太祖也算是一个奇人。某一天,躺在病床上的他,叫来族里人,将躺在靠椅上的他抬进族中的敬堂。敬堂是宗族的祖堂,比祠堂低一级。外太祖独自坐在敬堂里,飞仙而逝。
家中除了一柜书,再无长物,族人用一张芦席,将外太祖埋了。
母亲的大姐也就是我的大姨方桂枝尚未成年,自己都养不活,岂能养活两个年幼的妹妹?在族人主持下,将桂枝姨嫁给了范家坝叶家,再将二姨和母亲送给两户人家当了童养媳。
母亲去的这家姓何,是鄂城西山脚下菜农。此时的母亲,大约只有三四岁,由于出生时,其母多病,没有奶,靠吃藕粉薯粉维持生命,身体贫弱,极为瘦小。何家大概也不是富裕人生,生性节俭,加上主人性格乖僻,母亲的日子,便过得暗无天日。
我在少年时,曾听母亲忆苦思甜,略知道这段经历,母亲去世后,我又特别向父亲求证。
父亲说,那户姓何的人家,如果仅仅只是不给孩子吃饱,或者仅仅只是残酷地毒打孩子,尚可以理解。中国传统中,就有棍棒出孝子之说,打孩子是极其普遍的,几乎每个孩子,都有过少年被毒打的经历。
但是,这位何老先生显然就不是遵循传统,而是阴毒。
母亲年幼瀛弱,却被何老先生逼着干各种家务活以及农活,母亲只要稍稍出错,便会遭到一顿毒打。用来打她的工具是竹条,打在身上,不仅伤及皮肤,也会伤及衣物。为了衣服不因毒打而损坏,能够穿更长时间,何老先生想到一个办法,让母亲脱光。
若是亲生父亲,肯定不忍心将孩子打得过重。可这位何老先生,一旦动手,便无节制,往死里打。每次,母亲都被打得血痕累累,遍体鳞伤。治伤需要花钱,何老先生可舍不得,他因此想出一个独门绝技,逼着母亲喝尿。民间偏方,尿是可以治伤的。
母亲每挨一次打,便得喝好多天的尿,既喝她自己的尿,也喝家里其他人的尿,完全以尿当水喝。
除了因为家务活没有做好而挨打,更多的,还是因为吃而挨打。
母亲因为长期缺乏食物,食量其实很小。到了今天,我懂了其中的缘由,因为长期的饥饿,人的胃便会缩小,食量自然就会小。即使如此,在何家,她也吃不饱。何家毕竟也是贫穷人家,平常的食物,以杂粮为主,加点糙米。而母亲的碗里,从来都没有米,只有玉米红薯之类的杂粮,而且很少。
本就没有吃饱,还要干对于她这种年龄的孩子而言过于繁重的家务和农活,往往就饿得天旋地转,出错就是常事。一旦出错,必然挨一顿毒打。人毕竟有着顽强的求生本能,只要有机会,母亲就会捞到一切可以吃的东西,趁着何老先生不注意,匆忙塞进嘴里,囫囵吞下。
何家还有另一个童养媳,是为何家长子准备的,比母亲大好几岁,母亲叫她嫂子。嫂子见母亲可怜,有机会就偷偷藏一点可以裹腹的东西,找机会塞给母亲。
将东西塞给母亲只是一瞬间,可吃下去,却需要过程。这样的过程,很容易被何老先生发现,于是又会是一次毒打。
谁也不知道何老先生的心是什么组成的,毒打然后喝尿,似乎已经不能令他满意,他那农民的天才创造性,在一个雪夜里得到了极大的释放。
那个晚上,母亲因为饿得无法忍受,认定家人全部熟睡之后,偷了一把喂猪的米糠塞进嘴里。何老先生或许知道母亲今晚一定会偷吃,早已经躲在某处吧。母亲正艰难地嚼着粗糙的米糠时,何老先生拿着竹条突然出现。
于是,又是一场脱光衣服后的毒打,打过之后,是继续罚跪。门外下着雪,门内是刺骨的寒冷。谁都无法想象,强忍着满身伤痛跪在堂屋的母亲,到底经历着怎样的痛苦。
大家都认为军统审讯地下党时无所不用其极,但我从未见过任何文字记载,军统想到了这种折磨人的方法,这位何老先生却想到了,如果说他不是一个奇人,还真找不到比他更有畸形想象力的人了。
这个晚上,饥饿、寒冷、疼痛虽然集于一身,最终因为如山的困意袭来,母亲竟然跪着睡去,却又被大便憋醒。她不敢离开所跪的地方,又无法控制需要排泄,未能忍住,将一堆大便排在了何家堂屋。
清晨,何老先生起床了,母亲还躺在大便上昏睡,身上地上,一片狼藉。
何老先生也知道,昨晚已经将她毒打了一顿,恐怕再难承受另一次毒打。但不打,他又难平心中之怒,便再次发挥他那恶毒的想象力,拎着母亲的耳朵,将她提起来,逼着母亲将大便吃了下去。
这次实验令何老先生的想象力再一次大爆发。他或许想,你不是一直喊饿吗?那好,如果饿,那就吃大便吧。狗为什么吃屎?说明大便有营养嘛。
从此而始,除了毒打、罚跪之外,又增加了一项折磨,吃大便。不仅逼着母亲吃自己拉下的大便,也吃其他人拉下的大便。
何老先生的想象力继续发挥,不久又尝试像喂狗一样,用绳子牵了赤裸的母亲,去粪窖吃排出多时的大便。貌似更让何老先生兴奋的,是在大雪天完成这一伟大创举。
何老先生这些创举,令周围的人看不下去了,他们担心母亲会在不久因此死去,便有一个好心人,瞒着其他所有人,往范家坝大姐家传了一个口信,将母亲在何家所经历的一切,告诉了大姐。
此时的大姐虽已结婚,却仍然还是孩子,听说这一切,除了哭,再无办法。
姐夫毕竟年轻气盛,听说此事,肺都气炸了,当即叫了几个年轻的朋友,赶了几十里地,来到西山脚下,说是大姐想妹妹了,要将妹妹接过去住几天,也想接何老先生一并去住几天,以感谢养育之恩。
其实,姐夫和朋友们商量好了,此行既要将小妹骗出来,也要将何老先生骗出来。他们的计划是,一旦何老先生离开了西山脚下,远离了熟人,他们就将其毒打一顿。
不知是姐夫这些人太过年轻,脸上藏不住事,还是何老先生想到了事出蹊跷,刚刚离开西山不久,突然就不肯向前走。
就这样,母亲被其姐夫领了回来,这段地狱般的日子,才算结束。
三、母亲曾是童养媳
第一次知道母亲当童养媳的事,我还是一名小学生。具体是哪一年,我不记得了,当时的情景,给了少年的我极度震撼,因而印象极深。
那天是星期四,下午是老师铁定的政治学习时间,学生不用上学。我很快完成了家庭作业,然后就只有一件事,玩。
当时具体玩什么游戏,我不记得了,只记得我跑进了大伯家。那里正在开会,参会的,是生产队的全体成员。大伯家的长凳,惯例地由村里有些地位的男人坐了,其他人,自己从家里搬了小凳,或者坐在堂屋的角落,或者坐在偏屋。
乡村开会,是一大奇景。
前几天播出的电视剧《县委大院》,有围炉夜话一节,大家集中一处,由某人主讲,村民集中精神参与。其实,这个场景,与我记忆中的乡村开会,差的还不止一点距离。
在我的少年记忆中,村里开会,男人们坐在那里一根接一根抽烟,女人则多半在衲鞋帮或者鞋底,打毛线的极少,乡里穷,没几户人家买得起毛线。没有人带着茶杯一类的东西,乡里太穷了,且不说喝茶,白开水都不喝,实在渴了,到灶房里拿起水瓢,舀起水缸里的凉水,咕噜噜猛喝一气。
乡村开会的另一个奇景,就是孩子们在会场串来串去,从来不会有人喝斥制止。当然,孩子们也知道大人在办大事,不会大声喧哗,最多也就是跑进跑出而已。
这个星期四下午的会比以往任何一次都特别,我因为刚做完了作业,可以疯狂了,心情是大好的,又遇到村里开会,就有一种过节般的兴奋。我跑着跨进大伯家堂屋,就在双脚踏进去的那一瞬间,我傻眼了,屋里几乎所有女人,无论年纪大小,都在哭。
不是村里老了人的那种哭。
哭丧是湖北湖南一带的习俗,哭出的是一种唱腔,有旋律的。近几年,有人通过抖音表演哭丧,因而大火。
这个星期四下午,我所见到的哭,就是放肆地哭,无所顾忌地哭,难以控制地哭。这些女人们,是带了篮子篓子一类东西的,篮子篓子里装的是她们计划听会时要干的家务活。而此时,没有一个人还记得干活,只是哭了。
全村所有成年女人,竟然哭成稀里哗啦,这事实在太震撼。我意识到有什么特别的事发生,便不敢放肆地玩闹,同时也好奇,就跨进了偏屋,躲在角落里听。
于是,我听到一个女人在堂屋另一边偏屋里痛苦地哭诉的声音。是母亲,她在忆苦思甜。
忆苦思甜,是共产党早期搞革命发动群众时,一大极其有力的武器,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令民众凝聚起来。这一形式效果太好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十年间,忆苦思甜一直成为做群众工作的最为有效手段之一。
母亲在讲痛哭着讲述她少年时当童养媳的故事。
母亲说,那天下了一场大雪,外面的积雪有一尺多厚,天气极冷,是她记忆中最冷的一天。晚饭吃的是红薯糙米饭,她是这家的童养媳,男主人不准她吃多,也不让她吃主粮,只给了她几块红薯,她几口吃下去,连半饱都没有。
这家的男主人从来不给她吃主粮,只给她吃一点杂粮,而且量非常之少,那时的母亲,每时每刻处于严重饥饿之中。
熬到半夜,母亲认定全家人都睡了,便悄悄地爬起来,溜进偏屋。偏屋存放着粮食、农具等,为了防止母亲偷吃,男主人将存放粮食的柜子全部锁了起来,母亲能偷叫的,只有用来喂猪的糠。毕竟是饿急了,只要能吃,母亲顾不上了,抓了一把糠,塞进嘴里。
不料,男主人极其突然地出现了,随后,便命令母亲脱光衣服, 他拿起鞭子,对着她一阵猛抽,一鞭子下去,母亲幼嫩的身上,立即出现一道血痕。
即使如此,男主人还不解气,命令她将家中的长凳搬到堂屋中间,跪上去。
这种木凳只有约三十公分宽,一米多长,别说跪着,一个孩子,就算坐着,都可能坐不稳。
母亲屈于男主人的淫威,不得不跪上去。没一会儿时间,双膝跪得疼痛无法忍受,雪夜的寒冷,更是让她的肌肤如刀割般疼痛,她的身子稍稍一动,便从凳子上摔下来。
男主人又是一阵猛打,再次让她跪上去。又过不久,她再次掉下来,结果是再挨鞭抽。直到男主人打累了,也困了,严命她必须跪到明天早晨,如果明天早晨他起床,发现她没有跪在凳子上,一定要打死她。
说过之后,男主人去睡觉了。
母亲全身赤裸着,独自跪在堂屋的木凳上。虽然雪夜刺骨的寒冷,却经不住如山的困意。于是,母亲跪在凳子上打起了磕睡,一旦睡着,身体失去平衡,又会掉下来,同时也会摔醒。醒来之后,她又得自己跪上凳子,再一次睡着之后,又再一次掉下来。
那时的我年纪还小,不懂得愤怒,只有震撼和惊诧。我实在不知如何自处,便悄悄地溜了出去。出去后,又很想知道母亲接下来会讲些什么,在大伯的屋子边转了一圈,又悄悄地返回。
此时,母亲还在讲晚上罚跪的经历,我到现在都没有搞清楚,这是那个雪夜罚跪的继续,还是同样的经历,发生过许多次。从我隐约记得的片段分析,应该是另一次,因为这次不是跪在木凳上,而是跪在男主人的房间门口的地上。
同样是寸缕不着,同样是晚上。母亲跪着睡着了。睡着自然就无法跪稳,会摔倒,一旦摔倒,就必然醒来,醒来后,又得再次跪直。
这一晚,发生了一件特别的事,母亲无法控制地拉了堆大便。
如果是大点的孩子,知道要拉大便了,反正男主人睡得正香,自己偷偷跑出去,拉在粪窖里,然后再悄悄溜回来,神不在鬼不觉。可母亲年龄太小,五六岁的孩子,根本没有这样的心计。她害怕离开被男主人发现,又会挨一顿毒打。
大便拉在了堂屋的地上,又因为不断摔倒不断爬起,结果,大便被 母亲的身体滚得狼藉不堪,地上以及母亲的身上,满是大便。
第二天一早,男主人起床,见状大怒,不知他是不是认定母亲故意这么干的,第一时间抓过墙角的鞭子,照着母亲赤裸的身上一顿猛抽。抽累了,还没有完全解恨,命令母亲,将大便一点不剩地吃下去。
我实在不忍再听下去,又一次悄悄地溜出,再在大伯家转了一圈,又重新返回。因为数次进进出出,对于母亲的讲述,听得断断续续。
我再次进去时,听到母亲说,那家的男主人命她脱光了衣服,用绳子套在她的颈上,像牵狗一样,把她牵到自家的粪窖边,逼着吃下粪窖里的大便,前后有好几次。
我无法听下去,再一次溜了出来。
我们那个村叫河泾港,属于东风大队,更上一级单位,是华中师范学院大冶分院,分院的领导,是十四级干部,高干,隐约记得和黄石市平级。大冶分院属于当年的大学分支机构,合并了分院建立前的国营农场,农场的工人,成了分院的工人。此前的国营农场,下辖三个农村生产队,被称为过渡队,分别是南练山、北练山、河泾港。我们这个村,人数最少,男女老少,只有一百人左右。
在整个东风大队哪怕是整个大冶分院,大概再没有人比母亲更加苦大仇深。这一年的年末,母亲被评为什么积极分子,由大队颁发了一纸奖状,并且破天荒地给母亲评了八个工分。
生产队评工分是一件大事,关系到一家的经济命脉。一般壮劳力,一天可得十个工分,农忙时节如双抢等,最高一天可得十二个工分。女劳力,最高可评九个工分,农忙时节可以得到十一个工分。
父亲也是壮劳力,可他干一天,只能拿到八个工分,农忙时,最高也就是拿到九个工分,因为他是右%派,属于五%类$分#子。母亲受了影响,通常只评得六个工分,即使农忙时,最高也只能拿到七个工分。
这一年的年终,竟然破天荒给母亲评了八个工分,意味着未来的一年,母亲可以多拿七百多工分,能顶以前干一百多天的工分总数。
那天,母亲欢天喜地,与其说她高兴是因为拿了奖状,不如说是多拿了每天的两个工分。家里一直是超支大户,有了多出的这每天两个工分,家里当年的超支款,就能减少一大截。她的兴奋,也就可以理解。
可这股高兴劲没过几天,大队干部找她谈话,许诺把她树为全大队的典型,在全大队巡回忆苦思甜,甚至还会让她在整个华师大冶分院忆苦思甜,可能的话,还有可能去武汉,给整个华师的师生忆苦思甜。
但是,有一个条件,那就是要她和父亲划清界线。
母亲向父亲讲起此事,我只是听了个大概,并不完全清楚,上面希望她和父亲怎样划清界线,只知道,母亲拒绝了此事,因此便没有了任何后续,包括一年后,母亲的工分,又回到了六分
https://mp.weixin.qq.com/s/MozOPqcDSPInvtz_VrGYh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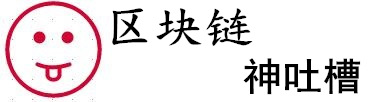 区块链神吐槽
区块链神吐槽